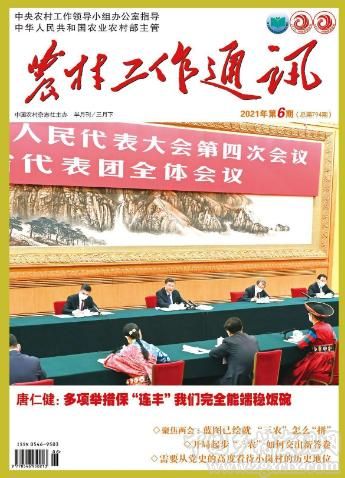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小崗村率先實行“大包干”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史詩般序幕,成為推動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這樣人類發展史上最為壯麗實踐的開路先鋒,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生動注腳。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如何看待小崗村,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需要從黨史的高度,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全面深刻把握小崗村改革的標志性意義,才能深刻把握黨在這個時期的歷史發展主題和發展主線。
小崗村改革:中國共產黨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黨領導農民在小崗村率先拉開改革開放大幕,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推動農村全面進步,使7億多人擺脫貧困,創造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奇跡。
不能回避,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身家性命危險簽訂大包干“生死狀”,是被長久以來的饑餓和貧困逼出來的。小崗村在“大躍進”中就餓死60人、死絕6戶,不論戶大戶小是戶戶外流,不論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討過飯。1978年夏收之時,小崗村每個勞動力才分到麥子3.5公斤,再這樣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條。如果有飯吃而不挨餓不討飯能夠活下去的話,幾千年以來就溫順老實的中國農民誰會愿意去冒坐牢的風險?
不能回避,改革開放前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走什么道路、向何處去的歷史抉擇。毛澤東在1974年的一次談話中就認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中國的客觀現實是“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的人口大國,是“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貧窮大國,已經處于“被開除球籍的邊緣”。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調查中發現,“一些農民過年連一頓餃子都吃不上”“農民碗里盛的是地瓜面和紅蘿卜櫻子混煮面成的黑乎乎的,霉爛的地瓜面散發著刺鼻的氣味”“全家幾口人只有一條褲子”。
根據有關資料,到1976年為止,“糧食增長率、人均占有糧食20年沒有增長”,其中1976年農村口糧比1957年人均減少4斤;1977年全國人平均口糧有1.4億人在300斤以下,明顯處于半饑餓狀態;到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占全國總數的29.5%的139萬個生產隊年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其中安徽全省的28萬個生產隊,能夠維持溫飽的有只10%,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隊占67%,人均年收入40元以下的隊占25%;在4000萬的安徽省農村人口中,就有3500萬以上的人不能維持溫飽。
根據林毅夫的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當年人均GDP的平均數是490美元,中國在改革前的GDP不到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的平均數的三分之一。全國居民高達84%的人生活在國際上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之下,其中有2億左右的貧困農民溫飽問題得不到解決,甚至有不少人處于赤貧狀況。因而“告別饑餓”“告別短缺”成為這一時期中國農民最主要的奮斗目標,對饑餓的恐懼是這一代農民最難以忘記的集體記憶。由于嚴格限制農民流動,1953年、1956年、1957年國務院分別下發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國務院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三份文件,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以改變貧困狀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農村率先改革引發和推動中國當代改革開放進程無疑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小崗村改革:中國共產黨遵循農業家庭經營的基本規律
經典作家曾判斷,“農民必將分化為農業資本家和農村雇傭勞動者”。但直至今天,經歷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強勢沖擊及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狂風惡浪,西歐、北美仍然是家庭經營為主體,日、韓仍然為東亞家庭小農。即使是美國的大規模農業,靠自身和家庭勞動力為主的家庭農場,1949-1997年始終占全美農場總數60%,到2007年上升到91%;工業化農業的企業農場則為1.31億英畝(占有耕地從20%下降到11.6%)。中國歷史上實行農業家庭經營延續了非常長的時間,到新中國成立的土改之后仍然是家庭經營,20世紀50年代中期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家庭經營變成集體經濟,1978年農村改革又回歸家庭經營,這個過程到底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認為,縱觀古今中外,這是一個必然。因為不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農業經營盡管存在規模大小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既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歷史現象,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普遍現象。
姚洋進一步認為,以家庭小農為代表的中國農業在清代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且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避免了西方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貧民窟大規模出現的問題。因此,以家庭經營為主體,作為農業發展的基本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唯意志論而無視客觀規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就必然遭到規律的懲罰,蘇聯“一大二公”集體化的人民公社經營模式壽終正寢就成為歷史答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從小崗村走向全國,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準確認識和把握農業發展的基本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從而讓農業回歸家庭經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撥亂反正。
不能違背,農業作為一種利用生物生命活動而進行生產的發展邏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經濟增長和自然增長相交織,不僅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市場規律,還要遵循生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工業的邏輯是集中、規模、高效率,是因為工業生產的對象一般是無機物或結束了生命的有機物,只要工藝相同,在任何地方生產的品質相同。而農業的邏輯是分散、適量、永存性,是因為農業是以自然界的生物作為勞動對象,是一種生命的邏輯,生命的邏輯要求分散,沒有分散就不可能發展下去,許多生物的生活只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高效,而什么樣的地域生態環境決定著生產什么樣品質的農產品,與工業標準化相比存在根本差別。
對于農業與工業存在勞動對象、生產方式的顯著區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明確指出,“農業上勞動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上勞動力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說明了農業的生產方式不同于工業的生產方式。馬克思進一步認為,農業的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與手工業的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是不一樣的。工業生產是勞動即生產、生產即勞動,勞動與生產是統一的,集體化生產和專業化分工可以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農業與工業相比具有自然再生產的獨特性,勞動即生產、但生產過程不一定都是勞動的過程,如手工業的勞動即生產,而畜牧業和種植業的生產過程并非全部是勞動的過程,故有些環節可以進行集體化生產和專業化分工,有些環節如自然再生產就根本不能;導致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存在著一系列不同的變化,由此決定了工業和農業的分配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不一樣。列寧當年就認為,俄與美相似而英法德的國情不同,所以要走美國農業發展道路,就要為“自由的農場主經營”“自由的業主經營自由的土地”掃清障礙,因而在十月革命前明確反對土地均分,土地綱領強調要分給農場主而不是分給懶漢農民,要求剝奪資產階級同時要求不能剝奪富農,因而在新經濟政策中提出勤勞富農是農業振興的中心人物,不要害怕農民的個人主義。說明列寧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意識到,農業以家庭為經營主體的方式,是由農業自身發展規律所決定的。斯大林修正了列寧的思想進行的蘇聯集體化實踐,簡單地按照工業的集體化勞動來發展農業,就是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這個自身規律,帶來了社會主義實踐仍然需要不斷反思的深刻教訓。
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問題是,規模經營是否就是耕地面積的規模呢?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論斷,就是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實質就是農業的技術裝備現代化。按照這個邏輯得出的第二個判斷,就是農地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就是,沒有耕地面積的規模就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也就不能用現代技術裝備來經營農業,結果就是無法實現農業現代化,也就成為集體化取代家庭經營的一個理論前提。因此,小農戶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詞,實現農業現代化就要走集體化大規模經營之路。今天中國農民的實踐也打破了小農戶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判斷。如湖南很多地方人均只有八分地,又大多是丘陵地帶和山區,盡管是這么小的規模,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實現機械化,都是用現代技術來裝備農業。還有河南、河北和東北等平原地區,實現了農機的跨區作業以及耕種一體化,不少地方甚至通過衛星導航和互聯網服務進行信息化的田間管理,小規模的家庭小農也能分享大機械的效率,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雖然每個小農沒有條件都購買農業機械設備,但通過農機社會化服務實現了現代化裝備,從而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規模經營概念,賦予了農業規模經營以新的時代內容,符合鄧小平提出“第二個飛躍”所明確的“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
針對“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大國小農”國情,十五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中國農業現代化就是社會化服務加家庭經營。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寫入憲法,標志著以土地承包為核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確立。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黨的十九大把家庭經營的“小農戶”第一次作為肯定性而非作為落后的否定性寫進黨的文獻,進一步回應了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
小崗村改革: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拉開改革開放的序幕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到小崗村考察時感慨道:“當年貼著身家性命干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志。”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小崗村的農民為解決溫飽、擺脫貧窮而在“大包干”字據上按下的紅手印,由此發端啟動了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制度變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拉開了對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大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
不可否認,小崗村改革為解決溫飽、擺脫貧窮的訴求是一條貫穿中國從近代到現代整個歷史進程的主線和主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成立以后,充分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把為廣大農民謀幸福作為重要使命。中國改革和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為什么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80%,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因此,最大限度地發展和解放生產力,更快地解決溫飽、擺脫貧窮就成了推進小崗村改革的最大社會共識。
為了公開接受用包產到戶的辦法解決長久以來困擾農村的貧困問題,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就明確表態,小崗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么資本主義,最多也莫過多收點糧食,吃飽肚子。小崗村以開路先鋒的作用恢復了農民家庭經營的方式,開啟了中國農村由“貧困饑餓”到“溫飽有余”的農業發展道路。1984年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的糧食過剩,1985年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農村消費占全國絕對比重的態勢,農村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占全國的64%,中國農民從此告別了饑餓的歷史。
隨著改革不斷推進,農村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鄉鎮企業的不斷興起,農民不斷從長時期困守的土地上解放出來,從根本上改變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以排頭兵和生力軍的作用開啟了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作為靠辛勤勞動最先好起來、收入最先多起來的“萬元戶”,都是來自最落后地區的農村、最貧窮群體的農民,成為當時改革的最大受益主體,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不可逆轉的社會基礎。作為現代化標志性的突破是允許農民進城,從而打開了隔離城鄉流動的閘門,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開啟了中國城鎮化的進程,實現了超越中國千年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化的歷史轉軌。
不可否認,小崗村改革破解了全球人口大國現代化的時代難題。作為全球特大型國家,既要以7%的土地養活約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又要以四十年的時間走過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歷程。如果不解決吃飯的問題,所有的改革、所有的主義都無從談起。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斷言:“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因為世界糧食市場的交易額是3億噸,全球農產品出口總量只能滿足5億人口的需求。1974年在羅馬召開的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一些專家就預判,中國絕無可能養活10億人口。因此,美國學者布朗就發出了“誰來養活中國”之問,最主要的就是基于對中國的三個基本判斷:未來人口不斷增長難以逆轉、耕地不斷減少難以逆轉、環境破壞造成農作物不斷減產難以逆轉。全力養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數人去從事農業,就是勞動密集型生產,工業化和城鎮化就不可能快速推進,就不能使社會財富快速增長,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始終處于落后國家的行列。如果以犧牲農業來成就工業化和城鎮化,即使能夠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誰能養活十多億人口的中國?
誰能想到,曾經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的小崗村,“大包干”后的第一年糧食總產量達十幾萬斤,相當于1955年至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350元,為1978年的18倍。誰能想到,相比改革前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積每年減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況下,從1984年廢除布票,到1992年廢除糧票;由不到十億人口連數量都無法滿足的食品短缺饑餓時代,到現在十四億人口卻農產品過剩而滿街的農產品賣不出、不僅要“舌尖上的安全”還要“舌尖上的美味”的時代,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水平的生產能力。盡管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但主要是進口大豆,接近糧食總進口量的80%。根據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大米和小麥全年進口量僅占當年產量的1.8%和2.3%,自給率均在95%以上;其中大米從2016年的進口數量逐年下降,到2019年同比下降53萬噸。根據商務部發布的數據,中國口糧年均消費量為2億多噸,2019年小麥、玉米、大米三大主糧庫存結余2.8億噸,庫存量可以確保全國一年的消費。
不可否認,尊重農民主體地位是推進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當時的體制沒有辦法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只能尊重基層探索、尊重農民首創,從包產到組再到包產到戶,由農民和基層先行先試再總結推廣。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鄧小平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其中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大膽地下放權力,尊重價值規律,尊重農民首創精神,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斷給予農民更多的生產自主權,讓農民成為生產主體,“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小崗村改革作為“應當相信大多數群眾,不要硬要群眾只能這樣不能那樣”的中國農民自發行動,盡管當時有過激烈的爭論,但由于得到鄧小平的力排眾議和大力支持,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自己決定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使小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國。
鄧小平感嘆,“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這是我們原來沒有預想到的”。正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推動了農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變革,成為改革的“原動力”。無論是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還是廣西合寨村的“村委會”選舉,或是華西村、大邱莊的鄉鎮企業,在備受爭議中得到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肯定與鼓勵而不斷完善走向全國,由此形成了鼓勵改革、激勵改革、寬容改革的時代精神,給基層與農民的首創實踐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臺,因而凝聚著全社會的改革共識和發展力量。
小崗村改革: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的時代標本
對于一個農民長期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古老農業大國,如何接受產生于西歐工業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對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命題。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一個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蘇聯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蘇聯模式”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范式,無疑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就認為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是必然的方式。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依靠全國人民“勒緊褲帶”搞建設的辦法,雖發揮了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農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鄧小平認為,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導致農業效率低下到了讓農民難以生存的地步。在社會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小崗村的“大包干”改革將農民從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生產經營主體以自主權,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中的人這個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人的創造性,由此出發推進了全球人口大國的現代化進程,與“蘇聯解體”作為人類史上最為矚目的興衰悲歌的事件相對應,小崗村改革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創新的時代標本。
小崗村改革的制度創新是什么?由于既經歷了“一大二公”的集體化道路的探索,其經驗與教訓成為今天寶貴財富;又目睹了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的發展歷程,其成就與缺陷可作為借鑒;從而就能夠充分發揮集體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的優勢,又避免了各自的局限,實現對人類史上兩種所有制的超越。這不是對兩種所有制的重復,而是集中了這兩種所有制的優勢,成為一種嶄新的所有制形式,無疑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不能混淆,改革前傳統農村集體經濟和改革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本質區別。就有人在質問,為什么小崗村過去包產到戶的,現在卻在大力發展集體經濟重走集體經濟道路?毫無疑問,改革前的傳統農村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農民沒有自由擇業的權利而終生守望土地,農民沒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權利而由政府統收統購,集體所有權以集體為主體單位,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改革后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產物,農民有自由擇業的權利特別是有進入城市的權利,農民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權利,在新農村建設以后又獲得了國家財政開始向農村投入的權利,在保持集體產權不變的前提下分離出承包經營權,進一步改革又分離出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實質上就是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以個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種形式為有機構成,成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因此,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決定著資源要素有機構成的多元性,決定著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是多種所有共同合作的混合經濟,從而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這就既發揮了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對發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對市場經濟的穩定作用,又激發了個人、股份、合作等多種所有的共同合作和發展活力,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各個方面發展農業農村的積極性。
不少人都把南街村、華西村等幾個村樹立為集體化道路的標本,從發展模式可以發現,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南街村、華西村的經濟結構是雙層結構,上層是由集體所有制構成,下層由資本構成。因為南街村、華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來勞動力和資金、技術等要素,既有集體的、還有個體的,還有股份的等,就是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如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000多個,卻有2萬個打工的外來勞動力以及資本,華西村也是這樣。因而有很多村集體成員外的資本參與經營和分配,實質上就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區域性、成員資格排他性的集體所有制經營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經濟形式。因此,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就要以明確什么是集體經濟為前提,因為現行法律框架下的農村土地是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以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土地等資產為基礎發展的經濟都是集體經濟,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那種“一大二公”的實現形式,無論是蘇聯和東歐的歷史還是中國的歷史都已經證明了是一條走不通的回頭路,決不能開歷史的倒車。
不能混淆,小崗村發展模式與華西村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有些人認為小崗村因為搞“大包干”是“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而華西村因為搞集體經濟走上了富裕道路。小崗村和華西村相比較,分別代表了農業和工業兩種不同的類型、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華西村主要是發展工商業,沒有多少農業,不靠種地賺錢,因而華西村發展模式是解決農業大國的工業化問題,是繼“大包干”之后被鄧小平稱之為“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標桿。華西村冒天下之大不韙率先辦起一家小五金廠,吳仁寶把工廠周邊用圍墻圍起來,不許外來人進入,與小崗村在“大包干”字據上按下紅手印一樣,也做好了坐牢的準備。后來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到1990年就成為中國“天下第一村”的“億元村”。因此,華西村以排頭兵的作用開啟了中國農村由“溫飽有余”到“富起來”的工業化道路。
小崗村主要是搞農業,制度變革所承擔著的歷史任務主要是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搞農業就是靠種地賺錢,而要農民靠種一畝三分地去共同富裕,無疑是在癡人說夢,這就是小崗村“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的根本原因。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不可逆轉,這是工業和農業之間經濟差異的歷史必然產物,是現代化進程中階段性的必然趨勢。即使是全面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農業已經成為資本高度集約化、技術高度密集型的現代產業,但效益與制造業、服務業相比是天淵之別。可以說,農業的持續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中任何國家都要應對的共同命題;農民平均年齡的不斷老化,是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特點。如強大的美國農業因務農辛苦、收入低,當前就存在著“誰來種田”的問題。華西村和小崗村一樣搞農業,能富嗎?難道全國農村學華西村都可以不搞農業嗎?
盡管農業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會或遲或早地必然成為弱勢產業,但任何時候吃飯問題永遠是比財富更重要的問題。因為不論多么工業化、城鎮化,任何人的軀體都必須仰賴農業而維系生存,任何人的生存都必須基于農業之中。因此,農業作為和生命休戚與共的戰略產業,與財富多少和富裕程度無關,因為無論多少錢都是不能吃的,對農業以追逐財富為導向的單純經濟價值功能,是“物本主義”登峰造極的結果。小崗村黨委副書記馬武俊說,“有的干部群眾看別的村發展工業富了,很著急,也想放棄農業大搞工業,說搞農業,五年十年都富不起來。”曾任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的沈浩定下過這樣的“規矩”:村里招商引資,一要涉農,二要能帶動農戶。“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擺在農業農村發展頭等重要位置,小崗村沒有忘記“以農為本”的改革初心,始終把土地、糧食看作安身立命的根基。
小崗村代表著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業村莊,不僅是解決中國溫飽問題的一個標桿,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整個中國“三農”問題的縮影。毫無疑問,中國農業的利潤遠遠低于社會的平均利潤,農民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卻徹底打破了“誰來養活中國”的中國崩潰論預言,中華民族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遠離饑餓的恐懼。然而,搞農業的小崗村不如搞工業的華西村富裕,搞農業的鄉村不如搞工業的城市富裕,就足以說明中國農民沒有獲得相應的經濟待遇,這是工農城鄉差別的二元體制下對農民的最大不公,也說明了中國農民作出了無與倫比的犧牲。
因此,小崗村太偉大了,中國農民太偉大了,中國全社會都要致敬小崗村!都要感恩農民!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21年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