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鄉村文化中,麻木是最為顯而易見的一種醒目的色彩。
麻木是一種病癥。醫學上十分明了地指出,由于神經系統發生某種疾患,身體的某一部分有螞蟻爬動的感覺,這種生理現象為之麻;而感覺的完全喪失,則為之木。“麻木”一詞從醫學向社會學的移植,是醫學的拓展,是社會學的進步。而把麻木的社會意義,專利于中國農民,則是社會學對農民偏激的深入。
如今,全社會都對農民的麻木深惡痛絕,甚至有些無可奈何。這種對農民麻木的認識,并非從魯迅開始,但自魯迅始,“農民的麻木與麻木的農民”之深入人心,卻要歸功于偉大的魯迅。《阿Q正傳》《祥林嫂》和《藥》等小說經典意義的深刻,怕正是與魯迅對“麻木的農民”的深刻認識密切相關;或者說,魯迅小說的深刻,正是他對中國“國民性”認識的深刻,而麻木則是魯迅認識到的“國民性”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麻木是“國民性”的軀干。一個寓意、象征麻木的人血饅頭,足可以警醒幾代農民和幾代中國各色的人群。
可惜,真正的農民并不看魯迅的小說。到了今天,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紀,華老栓早已死去,墳丘都已荒蕪,人血饅頭也不再有了,但麻木的農民和農民的麻木卻依然青枝綠葉,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為,包括魯迅先生在內的人們忽視了最關鍵的一點:麻木是生存中農民最有力的武器。
貧窮中的農民,如果他們連麻木都已沒了,那他們還有什么?魯迅的偉大,使后人不敢對他妄加評論,但我們是否可以斗膽地問魯迅一句:不讓華老栓用“蘸著人血的饅頭”對抗他華家的命運和華家所處的社會,那華老栓還如何能在那個社會中活將下來?正是因為農民把麻木當作了他們生存的武器,他們才一代代地生存了下來。
貧窮、饑餓、欺凌、無知、輟學、受人歧視、遭人譏嘲,土地的逐漸縮減,社會給農民帶來的不公,知識對農民的遺忘,戰爭給農民帶來災難,風雨對農民的不均吹降,物價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水平的停滯,政治對農民以安撫為手段的冷漠,經濟給農民帶來的躁動的無可奈何,任何一項,如果農民不用麻木來與之相抗,農民都將無法生存,都只能以死去來作為逃避。
對農民來說,沒有什么比麻木更有利于他們生存了。戰爭的降臨,他們手無寸鐵,眼看著馬蹄從莊稼地中踏將過去,刺刀扎進了人的胸脯,又明了反抗的直接結果就是莊稼更將倒臥,人頭更多地落地,唯有麻木才能使這些犧牲最小的話,他們就沒有理由不麻木。這是歷代戰史告訴他們的經驗,從奴隸社會開始,有哪一場戰爭不是因為農民的覺醒,農民的參與,而致使農民的終結更加慘痛?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國家的絕對人口,戰爭的災難無可選擇地最終要落在他們頭上。他們以麻木來忍受戰亂,以麻木來抵抗戰亂,甚至是用麻木來縮小戰亂的災難。面對疾病,面對無知,面對愚昧,面對婚姻道德和風俗沿襲,面對封閉的環境和因此世代無改的觀念,他們怎么辦?他們只能麻木。
麻木不是為了愚昧。麻木是為了生存。愚昧導致了麻木,麻木促使了活著。活著就需要麻木,只有麻木才能夠更好地活著。我們可以批判麻木,痛恨麻木,詛咒麻木,可我們在批判、在痛恨、在詛咒的時候,我們給他們創造了什么不讓他們麻木的條件?
他們什么都沒有了,權利、自由、平等,甚至溫飽,那么,如果再沒有了麻木,那他們會有什么?
二
農民最為深層的一道隱秘在于:他們物質上賴以生存的是土地、房舍、衣物,而精神上賴以生存的卻是常常同愚昧相混淆的麻木。麻木是他們生存狀態中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麻木是他們抗擊這個社會和周圍生存環境的最具戰斗力的精神武器。
是否可以說,麻木才是他們的信仰(我們可以剖析那些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農民,他們真的懂得天、地、神和上帝嗎?他們的信仰不正是麻木的又一種體現嗎?)。
由此,我們是否已經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對于農民來說,麻木未嘗全是壞事,它至少還幫助農民信心百倍地一代代延續、生存、發展了過來。
麻木成為武器——轉化為生存精神之后,它的積極性已經顯而易見。天旱歉收,雨水沖滌,饑寒交迫,農民的忍耐中又有幾分不是麻木?兵荒馬亂,無限殺戮,農民們血流成河,踩著尸體去收割播種,又有幾分不是麻木?麻木絕不僅僅是一種腐朽的文化和精神,同時也是農民生存戰斗的利器,與環境抗衡的砝碼。
我無以歌頌農民的麻木。麻木給農民和社會帶來了滿山遍野的災難,但我們仔細認識一番,就能清晰地看見,我們倡導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中,麻木是滲透其中的,如我們所說的忍耐、寬容、知足者常樂及勤勞和良善等,隸屬的農民那一部分,都是深含了麻木的。
至此,我們對麻木可以由以往深惡痛絕而轉化為相對溫和了。這不僅是對麻木的態度,也是對廣大農民和中國廣袤無垠的鄉村的態度。
三
我們還可以粗略而無結果地探究一下麻木產生的歷史根源,這有助于我們對麻木——農民生存的利器這一觀點的形成認識。在任何教科書上,我們找不到對農民麻木的形成注解。一些歷史書籍上也找不到這方面的注釋,但毫無疑問,原始社會,就是麻木存在,也不是作為一個觀念出現的。
農民的麻木,是對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而言。沒有工業文明,沒有脫離土地而依舊靠糧食維持生活的城鎮的最早的一群居民——還在農業文明的社會里,我們盡可以相信麻木的存在而在話語、概念、所指上都還沒有產生。正因為有了現代文明,正因為現代文明飛速發展到一定時期,農業文化成為現代文明進一步擴伸的阻撓,農民既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包袱。于是,農民的麻木,被明確地提了出來,被文明明確地痛惡起來,被都市和教科書及文化人批判起來,這也就集中地形成和豐富了麻木這一概念。
然而,我們一頁一頁地翻閱近代史頁,卻無論如何找不到一例消除農民麻木的事跡來。這也實在是大的悲哀,在一個農業大國里,幾千年的歷史長河,鄉村文化的驚濤駭浪和溪流水花,使河滿船高,而到了幾百年的近代文明時期,農業文明卻止步不前了,被歷史的腳步過早地踐踏了、遺忘了。當歷史再一次在文人筆下想起它時,剩下的已經只有批判和怒吼了,恨不得拉下馬后再踏上一只腳去了。
可是,農民不麻木又能如何?華老栓不用人血饅頭抵抗其命運,還有何妙方良藥?苗家的姑娘被人奸了,倘若狀告于政府,趙家的孩子必判其刑,這樣的結果,必然是苗家少女徹底在她生存的世界中失去“少女的身價”,而趙家的青年,在他的生存環境中,身敗名裂。經濟上、肉體上、精神上,將是苗、趙兩家兩敗俱傷,從此在那一隅地方抬頭不起。如此的結果,果真不如兩家同喜同樂,結為秦晉。
我們已經從小說也是真實故事的再現中,看到了所謂結好的過程,也就是麻木再現的過程。正是所謂麻木,幫助了苗、趙兩家,使兩難的尖銳迎刃而解,使事態朝“兩好”的方向轉而發展。
這里,我們可以批判麻木,但必須承認,麻木在苗、趙兩家,起到了通和的橋梁。麻木緩解了苗、趙兩家在外人看來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一事件上,麻木是某個鄉村某一時期平衡和睦最好的調和劑。
推而廣之,同樣可以說,農民個體間的麻木,一定程度和范圍是鄉村群落的平和劑;而農民集體的麻木,則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大砝碼,一旦農民從麻木中醒來,那種驚濤駭浪,勢如破竹的推翻打倒一切的力量,就將是無可阻撓要席卷一切的洪水。這方面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抗日戰爭之所以能持續八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民對入侵者的麻木。我的老家至今六十歲以上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都不說日本入侵中國的壞話:“老日呀,其實老日并不像電影上說的那么壞。日本人到了咱們村,還給小孩們洋糖吃,還給村里的老人送罐頭。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也就不惹你。”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八年的橫行與罪責,不正是和這種農民觸目驚心的麻木相關聯嗎?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幾次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不正是看到看透了這一點,才在土地革命的講話中,多次提醒那些革命領導人,“最重要的是,喚起農民的覺醒”。毛澤東把農民從麻木中搖醒了,毛澤東領導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木是有循環的。今天的農民,尤其今天的中國西北部農民,從舊的麻木中醒來,又到了新的麻木中去。當今醒目的貧富差別,東西、南北地區的差別,農民無可忍受的各種名目繁多的集資和稅收,以及驚人的地方干部魚肉百姓的事件,之所以都還依舊地滋生蔓延,甚至朝深廣處惡展,使我們都感覺到甚至還睡眠在社會穩定、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之中,所依賴的正是農民無意識的集體麻木,和把麻木習慣性地作為生存的武器和砝碼。
然而,農民若一夢而從麻木中醒來將是如何的境況?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太多的教訓。
更重要的問題是,目前農民正由個體轉為群體從新的麻木中蘇醒,而我們的社會還在繁花似錦的麻木夢中酣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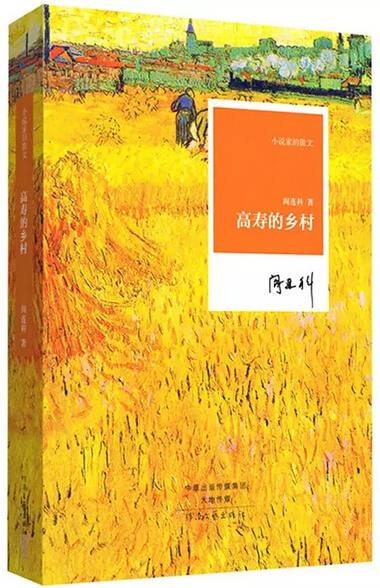
《高壽的鄉村》是著名作家閻連科最新散文自選集,收錄了以鄉村為主題的散文21篇,共分兩輯。作家重返憂思難忘的鄉土,用質樸的文字,平實的筆調,對土地、對家鄉、對親人、對童年的回憶,充滿無盡的溫情與心底的疼痛,既有理性的批判與反思,又有對農民給予深切的同情。該書是對鄉土中國的富于當代意識的重新關照與認識。
作者簡介:閻連科,生于1958年,中國著名作家,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二十幾種文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說家的散文:高壽的鄉村》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