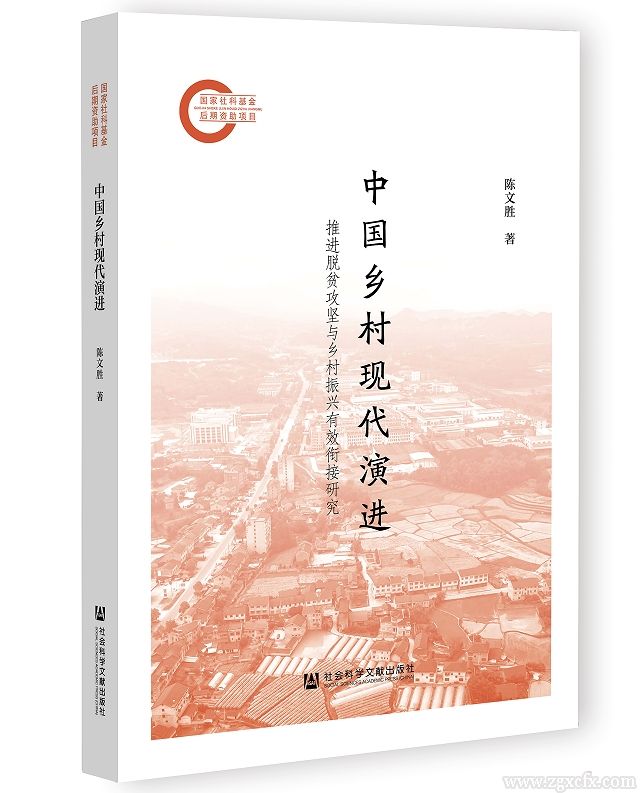
非常榮幸受文勝教授邀請來談到這次活動,2007年我在湖南省社科院參加工作時,文勝教授是社科院“三農”團隊里的“帶頭大哥”,也就是我們學科帶頭人。這使我想起了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里面的帶頭大哥玄慈方丈(在江湖上德高望重,玩笑話)。今天也沒準備,跟大家分享幾個觀點。因為我的工作經歷緣故,也就是在思想和行動間穿梭,我在社科院工作了9年,是專職從事經濟學研究和智庫工作,又在縣市基層工作了8年。剛才參加會議的有些領導可能行政工作經歷比我時間長久,在座各位教授可能學術研究經歷又比我深遠。但換個視角來看,可能我的研究職稱比一些領導要高一點,但是我基層工作經歷又比在座學者教授們的要豐富一點。
今天借這個機會,我主要和大家分享四個方面觀點:一是關于農民收入,二是關于城鄉二元制度,三是關于縣域發展的陷阱,四是農業的多功能及價值實現。
一是關于農民收入及結構。10多年前,我做關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關研究時,那時候農民的收入結構與今天的收入結構相比較發生了一些變化。大家知道農民的收入構成主要有四部分:農業生產的家庭經營性收入、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那個時候的家庭經營收入跟工資性收入基本是5:5的水平。剛才農業廳的副廳長講到目前農民的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已占到了70~80%,說明農民的收入和他們所經營的產業、從事的行業以及身份已經完全不匹配、不對稱了。這說明我們的城鄉關系、城鄉經濟結構進入了非常嚴重的割裂和撕裂的階段。這背后涉及到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人口城鎮化、農業人力資源開發和誰來種地等系列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央部署了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和以縣城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然而,從當前這種割裂的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來看,我們僅僅靠脫貧攻堅的幫扶和鄉村振興的政策支持可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城鄉融合的問題,而是需要從更高階的制度層面來解決問題。
為了更好理解當前農民收入結構,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大部分中西部縣的財政收入情況。湖南作為人口規模較大的中部省,是中央財政轉移致富最多的省份之一。我經常拿相當于全國經濟總量萬分之一體量的縣做比較。例如,中部地區大多數人口30-50萬人的縣,縣域GDP是100多個億,而全國是130萬億,這類縣的財政支出大概在30億左右,全國是30萬億,相當于萬分之一的樣子。但是中西部地區絕大多數縣一級的自有財力,地方收入大概是2-5個億。2023年,全國縣域GDP低于200億元的縣數量為1298個,這些縣大多數人均GDP低于4萬元,地方財政收入不到10億元,就連廣東省現有57縣市中有27個地方財政收入不到10億元。在當前土地財政不可持續的情況下,這些縣保工資、保民生、保運轉的財政支出90%要依賴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當然,這些轉移支付也是拿得心安理得的。我為什么說轉移支付可以拿得心安理得呢?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農民工的數量還有2.9億人,湖南也有近兩千萬人在沿海地區服務于新型工業化,服務于城市化,但是他們的社保、子女的教育、醫療保障都在戶籍所在地農村,這級的負擔是由縣一級財政承擔的。我們現在處于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二元分割的時期。經過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政策支持,看起來現在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要高于城鎮居民的增長速度,所以城鄉收入的比是不斷縮小,但是二元結構系數是不斷擴大的。我最近做了一個測算,比較農業和二三產業生產效率的二元結構系數大概是5~8倍的樣子,但是我們城鄉居民收入的比已經小于2了。
二是關于城鄉二元制度。剛才我講了城鄉融合發展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從制度設計層面發力。然而,我們國家一直實施的是優先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戰略,整個制度設置對農村和農民是非常不利的。我的個人觀點是,純粹的幫扶政策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的問題。關于貧困問題的研究,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領域,有很多經典著作和理論。剛才文勝院長書里面也引用了這兩本著作,一是阿馬迪亞.森《貧困與饑餓》,他是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二是班納吉和迪弗洛的《貧困的本質》,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這兩本書里面的觀點其實都值得我們借鑒。《貧困的本質》中講到貧困并不是因為缺衣少食。例如,最新的數據顯示當今世界上的貧困人口數量增加了,并不是世界上沒有足夠的食物,美國每年浪費的食物可能達到了30~40%;中國農業大學調查顯示,中國一年僅餐飲浪費的蛋白質就高達800萬噸,脂肪300萬噸,這相當于2億人一年的口糧。所以貧困的本質并不是沒有東西,沒有物質,而是這個物質怎么分配,怎么到達需要的人手上。因為制度的問題,因為政治體制的問題,導致了這些物質不能分配到所需要的人手上。按照如今世界上通用的貧困標準,全世界目前還有7億多貧困人口。自從2014年精準扶貧實施以來,中國花了很大力氣,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向全世界宣布我們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實現了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但是幫扶政策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呢?剛才大家也講了,經濟一波動,政府的聚焦力一旦漂離,一部分人可能又重新陷入貧困。京東董事長劉強東原來經常講一個觀點,他是1992年考的中國人民大學,那個時候可能有70%的同學是農村人口,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可能連10%的農村戶口的學生都沒有。現在一個在農村受教育成長的孩子要考上985高校的概率越來越低。我們看起來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本質上的城鄉之間的不平等不均衡還是在加劇。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制度設置,看起來出發點很好,最后卻變成了一種惡的結果。隨便舉一個例子,普高職高五五分流政策,看起來好像是讓一部分中學生盡快進入職業技術專業領域,更加切合新型工業化的人力資源需求。但這個制度事實的結果最后對農村不利,像湖南省如果按照普高職高五五分流,可能農村70%的孩子就要到職中去了。
關于制度政策的問題再舉一個例子,前段時間跟我原來共事過退居二線的縣委書記聊到這個問題,他們是懷化學院中文系81級的,他們講到一個81級現象,他們那一屆70個學生涌現出了各類拔尖人才,有從事文學創作成為省作協主席的,有從政擔任地市政協主席的,還出了幾個縣委書記。我后來跟他回了一句話,我說你再去查一下2001級,即我們這一代人懷化學院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就沒有這種跨越階層的現象,階層固化之后跨越階層的通道越來越艱難了。那個時代大學畢業包分配,他們基本上走上了各個行政崗位或者公職單位,他們通過一步步成長,都能在各自的崗位上比較順利地成長起來,哪怕是農村出身也有這樣的機會。現在的孩子,如果是懷化學院畢業的,靠自己考公比例是很低的。靠自己去當學者,再考研究生,考博士,可能這個通道好一點,沒那么固化。現行的制度體系下階層跨越的通道越來越狹小,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跨越階層越來越難。這表明很多制度設置的本質上來說,對農業農村和農民也是不利的。最后想通過幫扶這種短暫性的拯救式的方式,可能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三是關于縣域經濟發展面臨的幾大陷阱。大家知道,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報告里面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說人均GDP到了8000-12000美金的時候,發展可能會陷入困境,不能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區域來說,發展不均衡,內陸地區差不多就陷入了這個陷阱中了,大家也可以看到現在的經濟狀況。
由于中國1800多個縣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和階段,經過高速度增長的GDP“錦標賽”,各自所面臨的發展陷阱和困境也不一樣。中西部大多數縣處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階段,由于“土地財政”不可持續,縣級產業開發區等新的替代財源尚未形成,沉重的地方債務讓謀發展猶如“帶著鐐銬跳舞”,這些縣無法通過自生動力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階段躍遷。公開披露的貴州獨山縣2023年財政收入5.18億元億,各類債務總額達到400億元,借貸利息普遍是10%以上。有些縣正在經歷“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在人均GDP達到7000-12000美金的中等收入階段,由于各種因素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紛紛陷入經濟停滯或增長緩慢的狀態。我國一些縣市曾經一度憑借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獲得經濟快速增長,這些年由于資源枯竭、人力資源缺、社會不平等加劇、經濟結構單一、創新能力不足等導致縣域經濟增長停滯或放緩。有些縣還在經歷“斯蒂格利茨怪圈”,在國際資金循環中,新興市場國家以高成本從發達國家引進資金,然后再以低收益的形式將資金回流到發達國家,形成一種得不償失的資本流動怪圈現象。過去10年,大多數中西部縣域銀行存貸比長期低于50%,這意味著縣市居民以極低的利息把前存入銀行,而縣域發展所需的政府投資和社會投資需要以較高的利息借出來。由于縣級政府平臺公司由于缺乏抵押物,很長一段時間以年化利率高于10%的私募、信托、融資租賃等“非標”金融產品還本付息。這也是地方隱性債務形成的重要原因。總之,當前縣域經濟一個共同的特征是:背負著沉重的地方債務謀求快速發展,猶如“帶著鐐銬跳舞”;“以地謀財”不可持續后的縣級財政早已入不敷出,依靠“寅吃卯糧”勉強維持“三保”(保工資、保民生、保運中)。
四是關于農業的多功能性及價值實現。我們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它不僅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擁有經濟功能,還有社會功能和生態功能。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正式采用了農業多功能性提法。1996年世界糧食首腦會議通過的《羅馬宣言和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將考慮農業的多功能特點,促進農業和鄉村可持續發展。
農業多功能農業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態等功能的最大作用特點就是公共性,對全社會產生作用。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經濟基礎,更多體現其外部性和公共性,外部性是農業功能的基本特征;內部性和專用性功能只占農業總功能的一小部分。農業的多種功能并沒有在市場上得到價值實現,也就是說農業除了提供農產品的基本功能外,在調節生態、傳承文化、維持穩定等功能方面,表現為效用的外部性或公共性,個人和市場主體并沒有為其支付價格。例如,種植糧食比較效益低導致農民中糧積極性不高,而人口大國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地方政府必須壓實糧食播種面積的責任,這一現實矛盾一直是農民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兩難選擇,也是地方政府非農化非糧化整治的難題。我經常用地一個比方,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糧食還是一塊多錢一斤,隨便一瓶礦泉水都賣到兩塊錢一瓶了,這就是農業的多功能沒有實現。所以說,非糧化整治背景下提高種糧比較效益的模式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現在,國家發改委正在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試點,這也是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的有效方式。現代很多地方在創新農林產品生態價值實現模式,但是真正要這個機制實現,讓老百姓拿到收入的方式還是非常有限的。還有社會功能,我經常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一項農村經濟,農村集體經濟還具有民生功能和治理功能,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就不能簡單算經濟賬,那么它的民生功能和治理功能怎么實現,還需要繼續探索和創新。
這些年無論是脫貧攻堅期間還是現在的鄉村振興,農業和農村投入的資金并不少,湖南省每年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有效銜接的財政資金大概是在300-500個億的樣子,每個縣也是2-3個億不等。但是高標準農田建設也好,農田水利建設也好,都是以招投標項目化的形式落地,最后中間很大一筆資金是被各級施工方拿走了,真正落到實地改造的工程是很少的,當地老百姓得的實惠也是很少的。最近幾年國家發改委加大了“以工代賑”項目實施力度,在改造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條件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也能夠有效促進當地農民增收。今后,農業農村的項目實施可以考慮怎樣更好的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和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方面。
(作者系懷化開放大學校長、研究員,本文系作者于2024年12月8日在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研究研討會暨陳文勝教授《中國鄉村現代演進》新書發布會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