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勐臘河邊村扶貧已經有三年多了,最近我突然有些困惑。我們在河邊村還能干點什么?上次在村里的時候,我和一個農戶聊天,我知道他2017年從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里掙了七八千元。我說: “掙錢了吧?”,他說:“沒有,太少了,李老師”。按照勞動力計算,他們出去打工一天可以掙到100~150元,七八千元的收入相當于要打六十天以上的工才能夠掙到。村民出去打工一年累積到六十天以上的是不多的。他們種甘蔗,賣砂仁可以掙到一些錢。但是,像瑤族媽媽客房這樣基本上不用太多的勞動力,主要是瑤族婦女幫助收拾一下房間就可以獲得這樣的收入,在我看來已經很不錯了。我給農民講,你還不滿足啊。他說:“李老師,我們等著你帶領我們致富呢。”

“我們等著你帶我致富”這句話,讓我陷入了長時間的思考。我們能帶著他們致富嗎?馬云是千億富翁,他能帶著全國人民致富嗎?好像不行吧。農民想致富是天經地義的,就像我也想致富,后悔當年房價便宜的時候沒多買幾套房子。為什么當年就有人買了很多的房子而我沒買呢?我開始反思扶貧和致富這個問題,我們的政府官員,我們這些下去搞扶貧的人,躊躇滿志,告訴農民,扶貧你就能致富,告訴農民你們艱苦奮斗脫貧就能致富。仔細想一想我不禁暗自出汗。這是一個多么大的承諾啊!也可以說是個極其不負責任的承諾,我們在不經意中,抬高了我們幫扶對象的預期。而我們可能就根本達不到這種預期。我們可能自己在概念上混淆了“扶貧”和“致富”的關系。
扶貧和致富有沒有關系呢?當然有關系。很多人就是從貧困走向富裕的。所以我們要嚴格的界定我們說的“貧困”和“富裕”是什么概念。我剛開始在河邊村扶貧的時候和村民討論未來他們的房子,那個時候農民們都住在現在看來幾乎無法居住的房子里。我請搞建筑設計的志愿者把我設想的房子通過電腦做成彩色圖片,我跟志愿者講,一定要做成有顏色的,好看的房子。然后我做成PPT在我曾經用過的那個破舊、黑暗的辦公室里播放給村民看。村民都不相信,他們能住到那樣的房子里。今天村民們住上了比那個圖里面還要好的房子。政府通過組合性的扶貧資源為農戶擺脫貧困的狀態提供了支持。如果從一個福利的角度來看,河邊村算是脫貧了。為了讓農戶有一個能夠擺脫依賴甘蔗和砂仁收入的新的收入來源。我們設計了圍繞“瑤族媽媽”客房建設的一系列綜合的治理實驗。現在河邊村“瑤族媽媽”客房這個產業起來了。去年一年,有很多農戶客房加餐飲收入已經超過三萬元。即便是沒有餐飲的也都有一萬多元。我以為村民覺得自己脫貧了。但是我和很多村民聊天,他們還是講:“李老師,你還是要幫我們掙錢啊!”
今年以來,河邊村的很多村民都在學駕照,考到一個C證要花掉一萬元左右。我說你們都不想著投資再去掙點錢,就已經開始高消費了。有個年輕的村民跟我講,李老師,我看你們開車,我手也癢啊。這些其實都無可非議。正面講,我們中國的精準扶貧在政府的推動下能讓河邊村這樣一個貧困的村莊在三年內變成這個變樣子,恐怕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案例。
真正讓我思考的其實不是農民想致富的想法,而是我已經開始感覺到了我在河邊村做的這個實驗的真正的問題。我很少給村民開大會,三年多一共開過兩次。前一段時間,我給村民開會,我講河邊村發展的真正困難才剛剛開始。我覺得村民沒有太理解我說這話的含義。最近一年多,我和我的同事、學生的重點工作是開拓圍繞“瑤族媽媽”客房這樣一個產業的促進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學生們,經常都是加班加點做宣傳,聯系各種客源,簽訂各種合同,想盡一切辦法開具發票。我的同事、學生們幾乎都是現場的接待員。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農民的參與。不是說我們不希望他們參與,而是說所有這些工作農民都做不了。農民不知道這些工作是啥,是怎么做的。他們只知道某一天要來多少人住。所以我在會上告訴農民,我為什么說河邊建設的工作還沒開始,就是在說如果李老師和他的同事學生都撤走了,你們還能有這樣的收入嗎?我記得我剛說完這句話,很多農民就齊聲說:“李老師,你們可不能走啊!”
河邊實驗進入到了一個真正的挑戰階段。我和我的同事、學生們可能為農民做這些事情而永遠待在河邊村嗎?我突然覺得非常的內疚,一方面,盲目的把村民帶入到了一個預期很高的狀態。讓他們發展了一套與他們的技能、文化有著巨大差異的產業。現在又說,我們撤了你們怎么辦。自己覺得,這樣的扶貧似乎都不道義。當然,我們已經開始了通過建立合作社,確定各類工作的助理,從而培養農戶自主管理能力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我能夠清楚的認識到他們能夠掌握這些技能還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我們的河邊實驗所遇到的困境其實恰恰也說明了普遍存在的把深陷貧困陷阱的貧困群體帶上發展之路的艱難。其實,如果說有一個能專門為這些窮人服務的企業,他們來做我和我的同事、學生們現在所做的事情,那么河邊村的可持續脫貧還是有希望的。但是,這類企業或者民間組織在哪里呢?我在這幾年的公益界里宣傳公益資源下行的情況下,我甚至在勐臘縣注冊了“小云助貧”這樣一個小型民間組織。但是在基層,做這樣一個公益工作一方面沒有辦法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更重要的是招不到高素質的人才來做這樣的工作,連我的學生也沒有一個表示將來畢業會從事這樣一個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協助這些遠離現代市場經濟的群體在市場中逐步走向富裕在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卻很難;其次,如果這個村里能有一幫能人,自己組建一個文化旅游公司,那河邊村可能就真正有了生命力,但是在一個由親屬關系和傳統倫理維系的貧困社區,如果讓幾個農戶既有自身利益又需要為其他農戶服務,這樣的事情難度是很大的。這樣一個傳統社區去建立基于契約的社會關系難度是很大的。客源的分配稍有不公就會立刻導致契約關系的破壞。我和同事討論過,在將來合作社雇傭一個管理小團隊,通過向公益界申請來對這個團隊給以支持,然后隨著村里的會議旅游休閑發展起來之后,逐漸過渡到由合作社支付他們的費用。我和農戶開會講這個方案行嗎?似乎他們也很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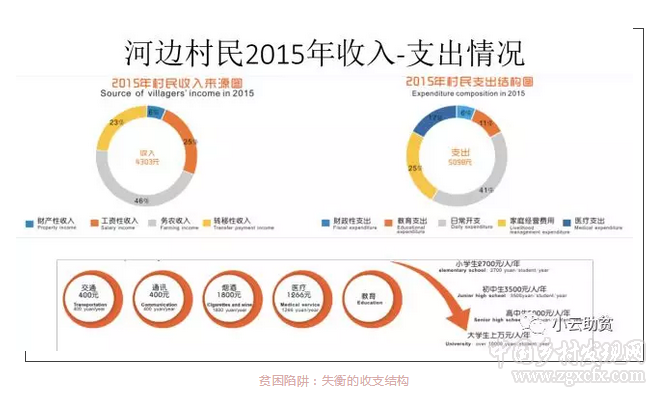
我和我的同事還有學生在河邊村的扶貧實踐中,認識到了可持續的扶持像河邊村這樣一個瑤族群體難度是很大的。這也讓我想到了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國家對于原住民的支持所存在的問題。雖然說這樣的比較不一定非常恰當,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是——當我們用一個現代的福利標準來衡量什么是貧困的時候,同時當我們又把一個我們自己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假設為他們也能遵循的路徑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給我們自己創造了這個困境。在這里,我沒有任何文化歧視和發展條件論的偏見。但在客觀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很多情況下,按照現代性倫理所設置的一個擺脫貧困和走向富裕的路徑并不總是有效的。我其實在這樣一個困境面前也是束手無策的。
我們在河邊村所做的工作在社會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無非是說,如何如何的成功。很多同事和朋友其實都不以為然,他們一方面看著我的面子說幾句表揚的話,另一方面,也覺得我三年來辛辛苦苦也值得表揚一下。其實我知道,我和我的同事還沒有摸到河邊村可持續脫貧的方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云助貧(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5-18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