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村落共同體的當代命運:四個觀察維度
提要:去社會學化、去社會理論化的村莊研究忽略了以下四個問題:(1)在批判社會學的視野里,村莊面臨市場力量的持續(xù)沖擊,后者要求土地和勞動力全部從共同體中分離,納入作為價格形成體系的市場。故村莊轉型的核心問題就是聽任市場力量,還是保留村落共同體。(2)在專業(yè)社會學的視野里,如果承認現(xiàn)代社會還需要小型、地方性共同體的存在,以滿足非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互助與交換,并發(fā)揮情感和社會認知方面的功能,就意味著要承認村落共同體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支撐條件在現(xiàn)代可能松動剝離,但它作為社區(qū)共同體仍然是正常的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資源;它能否在空前復雜的推壓力量下采取恰當?shù)摹斑^海策略”,實現(xiàn)與社會的聯(lián)結,首先取決于國家和社會把何種社會視為正常。(3)在公共社會學的視野里,地方性共同體是否被視為公民社會的敵人,首先取決于公民社會被視為應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之上還是方法論社群主義之上。從后一立場看,恰當?shù)拇迓涔餐w不是公民社會的敵人。(4)在政策社會學的視野里,國家應該在允許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同時,積極發(fā)展鄉(xiāng)村社區(qū),并且在解決城鄉(xiāng)社區(qū)的經(jīng)濟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基礎上發(fā)展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避免加快城市化與建設新農(nóng)村兩大國家戰(zhàn)略之間出現(xiàn)斷裂。
關鍵詞:村莊研究;村落共同體;社區(qū);城鄉(xiāng)銜接
*本文隸屬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卡特中心”)重大課題“農(nóng)村社區(qū)的成長、轉型與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問題研究”(07JJD630011)、教育部新世紀優(yōu)秀人才支持項目“中國農(nóng)民行動邏輯研究”(NCET -07-0749)。
中國目前還有60多萬個行政村,堪稱“村莊大國”。關注、研究中國村莊的生存、轉型和前景,是社會學的當然責任。然而,社會學學者研究村莊并非天然就是村莊的社會學研究。上個世紀90年代以降,村莊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是在這些研究——包括大量被冠以社會學名目的研究中,去社會學化、去社會理論化傾向很普遍;至少,村莊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lián)性相當模糊,社會學也未能在村莊研究中獲得多少知識更新、理論前進的有效動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在微觀技術上也許可以強調(diào)在單個村莊研究中運用布絡維的“拓展個案法”:將觀察拓展為參與,拓展時間和空間上的觀察從而發(fā)現(xiàn)社會情景與社會過程中的利益的聯(lián)系,進而拓展到發(fā)現(xiàn)社會機構的權力作用,以及拓展理論。由此,一方面“將反思性科學帶到民族志中,目的是從‘特殊’中抽取出‘一般’、從‘微觀’移動到‘宏觀’,并將‘現(xiàn)在’和‘過去’建立連接以預測‘未來’——所有這一切都依賴于事先存在的理”;另一方面也將“重點突出反思性研究的社會性嵌入”(布絡維,2007:77-135)。我相信,如果認真運用“拓展個案法”,每一個村莊研究都會成為社會學發(fā)揮作用并實現(xiàn)社會學自我更新的機會。在宏觀上,也可以從布絡維的社會學工作分類中找到糾正村莊研究去社會學化、去社會理論化的角度。布絡維從2004年開始一直倡言發(fā)展公共社會學。他提出社會學已經(jīng)形成了專業(yè)的、政策的、公共的、批判的四類分工。專業(yè)社會學提供真實、可檢驗的方法,積累起來的知識、定向問題以及概念框架,為政策社會學和公共社會學提供合法性和專業(yè)基礎。政策社會學服務于合同規(guī)定的某個目標,為客戶提出的問題提供答案。公共社會學要在社會學家與公眾之間建立公開的對話關系,其著述有非學術閱讀者,從而成為公共討論社會狀況的載體;社會學家通過公共社會學緊密聯(lián)系公共事務進行工作,目標是維護和促進公民社會的存在和成長,并達到對公民社會的認識。批判社會學則審查專業(yè)社會學的基礎,扮演專業(yè)社會學的良知,一如公共社會學承當政策社會學的良知(Burawoy,2005:7-10;布絡維,2007: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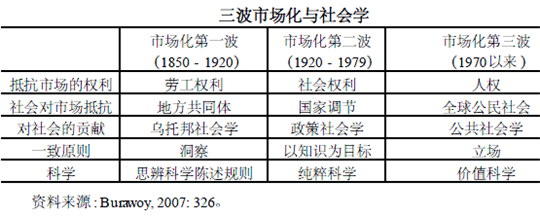
布絡維對社會學關注公共事務和公民社會的倡言雖然得到廣泛理解,但是他的社會學分類、公共社會學定位和謀求四類社會學之間的和解,在邏輯、修辭、可能性和影響諸方面都受到部分美國社會學家的尖銳批評(例如Brint ,2007)。然而,布絡維反駁說,這些批評完全出自專業(yè)社會學中的強綱領(the strongp rogram in p rofessional sociology ),而專業(yè)社會學強綱領所要求的純粹科學充滿了矛盾,并且是美國社會學早期發(fā)展的產(chǎn)物。他還以圖表概述其意見(見上表)。
本文不僅以擱置這些爭議的方式表示贊成布絡維,而且認為從布絡維提示的角度,可以發(fā)現(xiàn)村莊研究與社會學的緊密關聯(lián)性,發(fā)現(xiàn)一些解決村莊研究去社會學化、去社會理論化問題的可能性。
一、為什么要關心村莊轉型與村落共同體的命運:批判社會學的意識
從批判社會學的立場說,村莊研究不僅應該納入主流社會學的視野,而且社會學的村莊研究應該具有一個起碼的意識:在農(nóng)業(yè)人口居多的社會,農(nóng)民與村莊不僅注定是這個社會現(xiàn)代化、“常規(guī)化”的最拖后、最復雜、最深奧的部分,而且注定牽扯到這個社會究竟采取何種基本社會原則。這是因為一方面,村莊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現(xiàn)代國家進程的嚴重沖擊下仍然很頑強。①[據(jù)估計,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巨力推動下,未來25年中,發(fā)展中國家增長的90%人口將住在城市地區(qū)。但是到2025年,非洲和亞洲仍會有50%以下的人口、美洲和歐洲20%以下的人口生活在農(nóng)村地區(qū)(Virchow Braum ,2001:1)]村莊數(shù)量龐大而不易被整齊納入市場統(tǒng)治,它組織下的居民很難被平和而迅速地轉移,都是顯在原因,但尚屬次要;更主要的是村莊的存在一直基于地理、生產(chǎn)、文化和治理四個方面的條件,只要存在著糧食和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需要,存在著地理、文化、治理體系方面的支持,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村莊似乎就會繼續(xù)存在(Essex et al.,2005)。
另一方面,雖然很多人肯定鄉(xiāng)村地區(qū)在保證國家食物安全、保護自然資源、提供土地與人類息息相關這樣的價值體系,以及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有突出的貢獻(Flora Flora,2008:23),但是村莊的大量存在總被認為與現(xiàn)代社會不相稱,而市場力量對于村莊的敵意也幾乎不會改變,沖擊幾乎不可能停止。這種狀況及其性質(zhì)在韋伯和波蘭尼那里有很充分的解釋。依韋伯的分析,現(xiàn)代資本主義有兩方面的運作特征。
其一是圍繞盈利取向的工業(yè)企業(yè)及其制度性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理的會計核算及與此關聯(lián)的六項制度要素,即獨立經(jīng)營的私人企業(yè)可以任意處理土地、設備、機器等一切生產(chǎn)手段;市場自由;基于合理的會計技術之上的各種技術理性運用;可預測的法律法則;自由勞動力;經(jīng)濟生活的商業(yè)化,即普遍使用商業(yè)手段(金融工具)來表明企業(yè)所有權和財產(chǎn)所有權的份額。其二是企業(yè)家的資本主義精神,即視追求財富本身為人生的最大價值(韋伯,2006)。我們知道,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不等于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是最典型、最完整的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所以,資本主義進程至少表明,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所期待的制度設置、精神要素,在各種細節(jié)上(韋伯,2004)都與村莊的運行傳統(tǒng)、結構、制度處在不同軌道上,如果兩軌相并或交叉,不可能不對村莊的經(jīng)濟和社會產(chǎn)生否決性的沖擊。而波蘭尼則證明:資本主義市場力量不僅要求把貨幣、土地、勞動力都變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而且要求經(jīng)濟從社會中脫嵌,要求一切社會制度都轉向適應營利目標、效用原則,以便把社會變成市場社會(波蘭尼,2007)。按此要求,土地必須從農(nóng)民手中剝離;農(nóng)民必須作為自由勞動力個體從農(nóng)戶和村落共同體中分離,至多允許農(nóng)戶與村落共同體分解成經(jīng)濟合作體,并作為市場里弱勢的一員。因此,如果社會保護、國家保護方面沒有比資本更強大的力量和干預,市場力量斷然不會放棄對農(nóng)村社會特別是村落共同體的瓦解,雖然瓦解途徑多樣,有些在表面上似乎和緩,或者顯得與市場力量沒有直接關系。①[例如,交通事業(yè)發(fā)達,加速了社會人口流動;大眾傳播發(fā)達,影響了社區(qū)意識形態(tài);工廠制度發(fā)達,改變了社區(qū)生活方式;科層制度發(fā)達,改變了地方社區(qū)關系。這些都嚴重影響社區(qū)結構,導致社區(qū)的疏離和衰落,包括農(nóng)村社區(qū)(徐震,1980:1-6;Flora Flora,2008:13-14、19-20)。類似的重大影響因素顯然還包括全球化、網(wǎng)絡化等等,對于社區(qū)產(chǎn)生三種特別明顯的影響,即分解地方、加速流動、導致認同不穩(wěn)定(Day ,2006:182)]
現(xiàn)代市場力量渴求簡明的關系:一方是追求營利的資本,其他都是受資本支配的商品,以便擺脫一切社會公正的牽制而實現(xiàn)市場公正。
其中,作為生產(chǎn)主體的勞動者應與生產(chǎn)資料一樣成為純粹的商品(勞動者所需的生活物品也必須作為商品生產(chǎn)出來),資本與生產(chǎn)活動的主體之間才能建立起由資本全面支配勞動的、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關系。
因此,對市場力量而言,瓦解村落共同體和農(nóng)戶家庭共同體是必須的,甚至決定性的條件;因為無法設想共同體可以像自由勞動力個體一樣便于在市場交易——例如廉價購買一個農(nóng)民工的勞力時順便拖家?guī)Э谫徺I或照顧好他的全家,也無法設想這些自由勞動力個體進入市場、工廠后,繼續(xù)奉行村落共同體成員的原則和規(guī)范,使共同體規(guī)則影響或取代效用最大化原則。為此,市場力量不僅需要切斷勞動者與原共同體的聯(lián)系,“以便能夠作為工廠日后的員工而被重新調(diào)派”(鮑曼,2007:31),而且需要釜底抽薪,徹底摧毀共同體及其規(guī)則。鮑曼曾不失歷史感地勾勒資本主義市場力量反對與瓦解共同體的策略、進程和后果:資本主義制度是反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而資本主義的策略則是反共同體的。
在資本主義瓦解傳統(tǒng)的過程中,“自我維系和自我再生產(chǎn)的共同體,位居需要加以熔化(瓦解)的固體物(傳統(tǒng))名單的榜首”。所以,從工業(yè)化開始,市場力量一直全力以赴把勞動者從共同體中分離,并且“分解共同體的模式設定和角色設定的力量”,在經(jīng)濟領域與社會生活中剔除共同體,以便使脫離了共同體的個人凝結成為“勞動的大眾”。①[鮑曼(2007:27-41、47-54)認為這產(chǎn)生了兩個顯著社會結果。一是形成了個人化的社會以及虛假的全球化社會,從此,“管理就不是一件(可)選擇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需品”,因為“現(xiàn)代資本主義模式”需要的是服務于獲利動機的秩序和為秩序服務的東西,諸如建立全景式監(jiān)獄以便規(guī)范、監(jiān)視、控制、管理人們行為,用人為設計出來的規(guī)則慣例取代共同體的維系,以滿足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二是共同體破碎化后,除市場權貴聲稱不需要共同體之外,人們?yōu)榱嘶謴凸餐w體驗和獲得確定性,重新輕率地期待共同體。但是,“在新的權力結構框架內(nèi),恢復或從零開始創(chuàng)造一種‘共同體的感覺’”,顯然是“一種延誤了的努力”。所以,鮑曼寫道:再度聯(lián)結共同體的承諾,“可能預示著傷害要比收獲更多”,它不僅是用吸墨紙做成的紙筏,而且可能在獲救的機會已經(jīng)失去時才會被發(fā)現(xiàn)]
韋伯、波蘭尼和鮑曼共同提示了一條線索:市場力量在農(nóng)村的沖擊焦點是村落共同體和次一級共同體農(nóng)戶家庭,目的是把農(nóng)村勞動力和土地全部納入作為價格形成系統(tǒng)的市場,②[波蘭尼曾辨析過,市場有兩個概念,一個指根據(jù)慣例或法律交換物品的場所,另一個指作為價格形成系統(tǒng)的市場。共同體內(nèi)部不屬于后一種情況。施堅雅關于中國農(nóng)村市場體系的空間分布研究(施堅雅,1998)顯然混淆了這兩種市場及其社會后果的根本區(qū)別]接受資本的統(tǒng)治。而且,市場力量對共同體的敵意和瓦解,雖采取解放農(nóng)村自由勞動力的激進姿態(tài),并不能遮掩它是要求經(jīng)濟從社會脫嵌并以市場自由規(guī)則支配社會的組成部分;使勞動力脫離家庭和鄉(xiāng)村是為了讓他們擔當兩個角色:為資本主義生產(chǎn)廉價商品、作為廉價勞動力本身(B rass,2005)——正是這種要求使市場力量在本性上不會放棄對村莊社會的沖擊。
應該說,面對市場力量的持續(xù)沖擊,已經(jīng)沒有多少人會認為村莊可以不變化、不適應、不轉型。地方性自治實體和共同體意義上的村莊顯然很難抵抗不同尋常的市場力量(Day ,2006:152-153)。為此,這十多年間很多農(nóng)民研究者實際上已轉向兩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向第三世界農(nóng)村地區(qū)擴張的情況下,農(nóng)民可以在什么范圍和什么程度上幸存(Brass ,2005)。但是,由于市場力量對農(nóng)村、農(nóng)民的沖擊根本上就是對共同體的沖擊,村莊轉型的根本難題主要是村落共同體問題,因此關鍵性的爭議也就在于:村莊轉型究竟是采取農(nóng)民變?yōu)樽杂蓜趧恿€體的方式,還是保留共同體的方式?村莊作為農(nóng)民、農(nóng)業(yè)的傳統(tǒng)的重要聚集單位,是否還有代價最小的融入現(xiàn)代社會的通道?在融入過程中,村莊單位中某些要素的保存是否具有社會意義?其中特別尖銳的問題就是,村莊居民都轉變?yōu)橐詡€體為單位的自由勞動力,是市場力量的要求,但農(nóng)民通常要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并通常會成為市場中的弱者。社會、國家究竟該如何對待這些村莊及其居民?這顯然不僅是一個經(jīng)濟學上的效用計算問題,更是一個與社會態(tài)度與社會立場相關的問題,其本質(zhì)是如何對待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即是否支持經(jīng)濟從社會中脫嵌。
在我看來,目前多數(shù)主流經(jīng)濟學家關于農(nóng)村勞動力大幅度轉移與城市化的常規(guī)性理論與計劃,基本上是基于發(fā)達國家資本主義進程的一般抽象和展望——在這種展望中農(nóng)民和村莊只有數(shù)字意義,完全忽略了農(nóng)民變成單個勞動力、村莊瓦解過程中農(nóng)民和村莊可能付出的代價,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問題,村落共同體的命運幾乎被置若罔聞。倒過來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發(fā)揮小農(nóng)戶作用、以農(nóng)業(yè)促發(fā)展、主張扶持農(nóng)戶以合作社進市場的理論與計劃(世界銀行,2008),雖然其同情農(nóng)民、重視農(nóng)業(yè)、要求經(jīng)濟與社會協(xié)調(diào)的立場值得尊敬,并富有經(jīng)濟學的想象力,但是多少有點低估市場化力量及其對村莊的“敵意”。事實上,20世紀后半期在全球各地出現(xiàn)的重建鄉(xiāng)村地區(qū)、保護農(nóng)民權力和鄉(xiāng)村活力的“新鄉(xiāng)村社會運動”,雖然贏得了重大進展,但也迫使研究者們重新審視以下一系列復雜論題:“鄉(xiāng)土性”在規(guī)制社會運動的性質(zhì)、對象和修辭方面承擔了什么角色?在社會和經(jīng)濟變遷的背景下,社會運動在重構鄉(xiāng)村地位方面的角色是什么?在當代鄉(xiāng)村政治參與方面,鄉(xiāng)村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告訴了我們什么?鄉(xiāng)村社會運動之間、鄉(xiāng)村社會運動與其他組織之間的聯(lián)盟是怎樣的?是什么因素賦予了鄉(xiāng)村社會運動構成及其動員以地理特征(Woods ,2008)?這些問題都應該受到社會學,特別是農(nóng)村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的關注。
在中國,60多萬個行政村及其涉及的村落共同體向何處去,顯然是牽扯全局的問題,不僅關乎農(nóng)民,也關乎整個中國市場經(jīng)濟、整個中國社會的將來。什么是村落共同體?它是否值得在社區(qū)脫域化和居民個體化趨勢下生存、適應與轉型,有沒有未來?這都是需要倍加關心的大問題,不僅作為社會學分枝的農(nóng)村社會學要加入研究,而且完全應該進入主流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以便一方面克服單純依靠常識觀察重大社會問題的缺陷,另一方面省察社會學的知識更新和社會責任。在此意義上,每一個村莊及其轉型方式,表面上微不足道,本質(zhì)上茲事體大。
坦率說,沒有這一個層面的關心,關于村莊的個案研究多半看似富有現(xiàn)實感,實際上沒有現(xiàn)實感,能夠生產(chǎn)的只是雞零狗碎的地方故事,而一些看似更加雞零狗碎實際上極為重要的東西,又將被過濾殆凈。
二、村落共同體作為小型地方性共同體的現(xiàn)代命運:專業(yè)社會學的維度
如果專業(yè)社會學接受上述判斷并且關注村莊轉型及村落共同體的命運,那就需要重新關心現(xiàn)代社會是否還有小型、地域性或地方性共同體的存在余地和需要,關心這種共同體與社會的關系。由于共同體或社區(qū)(community)的討論從來都涉及人們究竟是如何聚集成社會這個社會學的一貫主題,因此,這種關心不僅間接地反對社會消失論,①[山口重克(2007:中文版序)曾批評說:“現(xiàn)在,源于主流經(jīng)濟學派的市場原理主義的怪物正在世界上空徘徊,美國式的市場經(jīng)濟全球化也正在向全世界蔓延”。這正是社會消失論的兩個支持背景。前者是指,市場力量固然力求經(jīng)濟與社會關系、社會規(guī)則脫嵌,要求用市場規(guī)則支配社會關系或只保護社會紐帶中的貨幣關系紐帶,但實際上從來不曾存在完全不受國家規(guī)制的市場經(jīng)濟,社會也并未真正允許過這樣的脫嵌(波蘭尼,2007;山口重克,2007)。然而,新古典經(jīng)濟學堅持經(jīng)濟從社會中抽離,堅稱市場能理順一切關系,還是相當程度地模糊了經(jīng)濟仍嵌入社會的事實,社會似乎已是一個無意義的概稱。至于村莊與其他小型社會共同體更是舊社會的古怪殘余,將很快被市場掃凈。后者是指全球化進程助長了一個古怪的后社會理論判斷。即文化分裂與跨文化交流稀少,在歷史上、在古典社會學和一些人類學家那里的確曾被視為一個共同體形成和存在的必要條件。一種有影響的后社會理論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地方性的社會已經(jīng)無可奈何、無足輕重,霍布斯以來社會科學所討論的國家管理下的“社會”已消失在全球化、信息化、互聯(lián)網(wǎng)之中。顯然,如果社會真已消失,包括村落共同體在內(nèi)的所有社會共同體自然是無需關心的多余問題。不過,絕大多數(shù)社會學研究者都會認為社會實在論根本毋庸爭議,社會消失論只是華麗而虛枉的論斷(梅勒,2009:1)。因此,這里不遑直接論辯,而是準備反一個方向去觀察共同體存在的基礎和意義,從而觀察共同體問題是否還能夠繼續(xù)或重新成為社會學的嚴肅論題。如果農(nóng)村社區(qū)這類小型、親密、地方性共同體都繼續(xù)存在,并具有意義,社會消失與否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助于解釋社會究竟是如何結成的]而且意味著要再次反省關于共同體和鄉(xiāng)村社區(qū)已經(jīng)消失在大眾社會中的社會學判斷。
應該承認,自滕尼斯1881年作出Gemeinschaft(通常譯為共同體、集體、公社、社區(qū)等)和Gesellschaft(通常譯作社會、社團、聯(lián)合體等)的類型學劃分,以及涂爾干早期區(qū)分機械團結社會與有機團結社會以來(涂爾干后來放棄了早期的意見),共同體、社區(qū)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區(qū)或共同體的前景一直被置于相對黯淡的通道內(nèi)。與韋伯把共同體(community)和聯(lián)合體(association)視為連續(xù)、混合地存在于社會關系中的觀察不同(韋伯,2004),大多數(shù)人不僅把它們視為對立的、相互排斥的兩方(Day ,2006:5),而且多少有點憂郁地預計社會興盛、共同體衰竭是不可逆轉的。①[滕尼斯強調(diào)兩種類型本身只是抽象的理想類型、極端形式,用以觀察實存的社會關系類型,后者實際上是動態(tài)的,在社會時期共同體作為衰退的力量甚至也會存留。但是,他的確強調(diào)過村莊共同體是Gemeinschaft的突出例子。所以,通常Gemeinschaft代表“舊”、自然的、同質(zhì)化,而Gesellschaft意味著“新”、理性化、異質(zhì)化、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滕尼斯還提到Gemeinschaft在市鎮(zhèn)、工作團體和宗教團體中可以達到新的水平,但城市則是它的終極敵人(Day ,2006:5-7)。強調(diào)共同體的自然、有機性,并認為它代表著某種相對的穩(wěn)定與同質(zhì)化,的確很容易令人認為共同體屬于舊的社會秩序(Noble ,2000)。而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和社會異質(zhì)化程度提高,顯然支持了人們更多地注意兩者的對立,以及非共同體關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持續(xù)擴張現(xiàn)象,從而把社會聯(lián)合體大量興起且與共同體并存的情況理解為前者逐漸取代后者,如雷德菲德強調(diào)俗民社區(qū)與都市社區(qū)之間存在著連續(xù)性變化(Redfield,1947),實際上就是指社區(qū)向社會的變遷是一個連續(xù)的過程]1960年代,沃倫甚至提出了一個具體模型解釋社區(qū)與社會的關系及社區(qū)變遷:社區(qū)存在著縱與橫兩種關系;縱向或垂直軸面的關系指社區(qū)內(nèi)各社會單位與超社區(qū)組織(諸如區(qū)域性、州級、全國性組織)之間的關系;橫向或水平軸面的關系是指社區(qū)內(nèi)個人與個人間以及團體間的關系。依此模型描述,現(xiàn)代社區(qū)變化的特征是社區(qū)的縱向關系強化而橫向關系趨弱,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即社區(qū)中超地方的力量逐漸破壞社區(qū)的水平整合(horizon integration),小型鄉(xiāng)村社區(qū)變得無力面對強大的城市化、工業(yè)化、中產(chǎn)階級化和中心化的力量。這些宏觀進程產(chǎn)生的社會組織變遷已經(jīng)使鄉(xiāng)村社區(qū)無法依舊自治,并把它們吸納進了大眾社會(Warren,1963)。基于大眾社會已經(jīng)淹沒了社區(qū)的判斷,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實際上不再把鄉(xiāng)村社區(qū)作為研究對象(Gallaher Padfield,1980)。70年代末情況發(fā)生轉變,雖然信息時代、網(wǎng)絡社會、全球化在一些人看來更加意味著傳統(tǒng)社會和共有認同的解體,表明社區(qū)研究越來越失去意義,但是另有許多研究者意識到共同體、社區(qū),包括鄉(xiāng)村社區(qū)消失論屬于言過其實,垂直整合進程沒有削弱,至少沒有取消社區(qū)水平整合,當代社會學需要在自己的核心保持一種原則,即繼續(xù)把共同體視為社會組織、社會存在和社會經(jīng)驗的一種形式(Almgren ,2000)。①沃倫本人在《美國社區(qū)》1972年第二版中也承認社區(qū)死亡論是一種夸張,在1978第三版中則提出宏觀系統(tǒng)會對社區(qū)發(fā)生有力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完全決定和替代了地方,許多地方結構與行為首先是在地方水平上規(guī)定的,社區(qū)仍然可以相對自治(Summers,1986)[]人們甚至開始用共同體或社區(qū)的“喪失”、“拯救”和“解放”標示社區(qū)觀點隨時代而更新的過程,即社區(qū)“喪失”論是基于工業(yè)化時期城市和城鎮(zhèn)大量興起的社會經(jīng)驗,社區(qū)“拯救”的主張基于社區(qū)與共同體關系繼續(xù)存在于工業(yè)化的城市社會的現(xiàn)實,而社區(qū)“解放”觀點則基于社區(qū)紐帶的空間依賴將被流動性和通信便利所取代(Wellman Leighton,1979)。此后伴隨著社會資本理論的流行,在社會學中出現(xiàn)了所謂共同體或社區(qū)概念復興的現(xiàn)象(Vaisey,2007)。人們甚至觀察到在反對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剝奪的人們中間,存在著針對全球化和激進個人主義的抗拒性認同和接受共同體的認同,其中包括以地域認同反抗作為信息社會統(tǒng)治特征的流動空間的無場所邏輯,這才是信息時代的潛在主體(卡斯特,2006a,2006b)。在我看來,這個轉向有益于認識有關共同體、社區(qū)的現(xiàn)代意義,并使農(nóng)村社區(qū)發(fā)展、城市社區(qū)建設的實務不至于淪為沒有前景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市場力量對于廣大村落共同體的敵意,以及村落共同體可能面臨的轉型陷阱,那么就有必要特別深思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社區(qū)作為地域性的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仍然被需要;地域或地方特征并不表示社區(qū)共同體悖時,關鍵是地域性共同體(例如社區(qū))是否能建立起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共同體與更大社會之間的聯(lián)合體。
與滕尼斯一開始就從地域條件、社會關系以及文化一致性兩方面同時定義Gemeinschaft有關,②[滕尼斯把Gemeinschaft分為三種類型:1、地理的社區(qū),以共同的居住區(qū)及對周圍(或附近)財產(chǎn)的共同所有權為基礎。鄰里、村莊、城鎮(zhèn)等都屬這種社區(qū)。2、非地區(qū)社區(qū),亦稱精神社區(qū),只內(nèi)含著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進行的合作和協(xié)調(diào)行動,與地理區(qū)位無關,如宗教團體和某種職業(yè)群體等。3、親屬社區(qū),也稱血緣社區(qū),即由具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成員構成的社區(qū)。所以,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文化去觀察、定義社區(qū),都會有滕尼斯的影子]一方面從齊默爾曼(CarleC.Zimmer2man)開始,共同體的地理要素被社會學所強調(diào),社會學常識意義上的共同體(community)一度主要指自然的、地域性、小型的、成員彼此熟悉、日常互動頻繁、相互幫助的、有某種共同生活方式的團體——這些條件支持著作為組織、范圍內(nèi)的、實體(都經(jīng)常與地方和區(qū)域相聯(lián))內(nèi)的成員相互依賴的、感情的紐帶。小鎮(zhèn)社區(qū)方面林德夫婦(Robert S.Lynd HelenM.Lynd )著名的中鎮(zhèn)研究、沃納(W.L loydWarner)的揚基城研究,村莊社區(qū)方面艾瑞森伯格與肯波(C.M.Arensberg S.T.Kimball )對愛爾蘭西南部鄉(xiāng)村的研究,工人階級社區(qū)方面格林(Bethnal Green )關于倫敦東區(qū)工人社區(qū)的研究,都支持從地方性定義社區(qū)共同體。漢語社會學所表述的“社區(qū)”(也就是聚居共同體)即是家庭共同體之外最典型的地域性共同體,接近于韋伯所注意的“鄰人共同體”,①[韋伯極其注意并強調(diào)大多數(shù)社會關系中存在著自然的集體特征,即社會行動者并非只關心自己的興趣,而幾乎總是留意其他人的希望、需求和行為。在人們卷入社會互動之處,總會發(fā)現(xiàn)共同體的潛在可能性,那些持續(xù)性的聯(lián)系會特別產(chǎn)生互相依存的共同感覺。在這類關系中,除了軍隊單位、班級、車間、辦公室以及情同兄弟的宗教團體等例證外,韋伯特別注意到,鄰居的近距離是他們相互依賴感特別真切的根源,鄰居正是所需要的典型的幫助者。鄰居特別表現(xiàn)了組成興趣共同體的傾向(韋伯,2004)]或者說是鄰人共同體的規(guī)整(甚至是極限)形態(tài);村落共同體則是指農(nóng)村社區(qū)意義上的共同體。相反,社團或聯(lián)合體代表著處在不基于地域邊界的、契約關系內(nèi)的人們之間的交流關系,彼此之間的紐帶僅僅是便利。②[在此意義上說,固然最好把社區(qū)和共同體加以區(qū)分,以便區(qū)分和定位家庭共同體、社區(qū)共同體、農(nóng)村社區(qū)共同體即村落共同體等等,但在本質(zhì)上,英語社會學術語對共同體和社區(qū)不加區(qū)分,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妥;費孝通以社區(qū)(聚居共同體)譯community 也并無不妥]但是另一方面,共同體的社會關系類型、文化類型的要素,也頗受社會學的關注。特別是當代一些主張共同體存在而且應該存在、但又認為現(xiàn)代常規(guī)社會采取而且應該采取聯(lián)合體關系類型的社會學家,通常強調(diào)地域條件不再是共同體的必需要求,共同體只是“指人們共有某些東西,它把人們緊緊連在一起,而且給人們一種彼此相屬的感覺”(Day ,2006:1),即它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結合團體:人們在其中互相幫助以滿足需求,彼此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和可以分享的文化,有一些團結紐帶以維持這個團體。所以,小至于家庭與社區(qū)、大而至于國家的結合團體,只要有這些特征都可以視為共同體。而傳統(tǒng)共同體范式不再能容納當代現(xiàn)實(Bernard ,1973),更像一個哲學夢想而不是真實現(xiàn)象(Day ,2006:9-10)。按維塞的分類(Vaisey,2007),當代社會學中強調(diào)共同體的地域條件的解釋,屬于共同體的結構主義理論,它主張共同體基于4方面機制:時間空間性互動、類似性、權威以及收益。這是一種基于組織要素、環(huán)境條件的共同體機制分析,主要在社會網(wǎng)絡、社會資本理論(Brint ,2001)和美國新城市主義理論(Calthorpe ,1993;Kaitz,1994)中得到集中表述。而主張共同體首先基于共享性道德秩序的觀點則屬于共同體的實質(zhì)性理論,它強調(diào)共有道德秩序會在面對面交往的團體中激發(fā)一種歸屬感。這是一種基于文化意義、道德產(chǎn)物的共同體機制分析,主要在澤奧尼對普特南等人的批評(Etzioni,2001)、泰勒的社群主義理論及其在社會學理論方面的延伸(Colhaun ,1991;Smith,1998,2003)中得到集中表述。
實質(zhì)性理論有利于認識共同體在當代社會的存在及其價值,但是,把所有的社會結合體都泛視為共同體,降低甚至取消共同體的地域性質(zhì),并不見得明智。這不僅因為大多數(shù)社會學家們觀察到地域性團體仍然是共同體普遍的、關鍵性的特征,①[奧姆格林指出:齊默爾曼(Zimmerman,1938)關于社區(qū)或共同體的經(jīng)典定義包含4個特征:社會事實、規(guī)范、聯(lián)合、有限地區(qū);它需要一種區(qū)域性內(nèi)容。希拉瑞(Hillary ,1955)分析了既存的94種社區(qū)定義后,發(fā)現(xiàn)它們基本集中在3個因素上:人們之間的社會互動、一個或更多的共有紐帶,以及一種地域關系。希拉瑞提出地域關系是最基礎的元素。其他研究者(McMillan Chavis,1986)則認為只要社會網(wǎng)絡充分到足以維持Gemeischaft 水平的互動與協(xié)作,社區(qū)就能存立;所以區(qū)域對于社區(qū)或共同體而言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麥克米蘭和查維斯提出只要4個元素同時存在即可視如社區(qū)或共同體的狀態(tài):成員資格、影響、整合與需要的滿足,以及共同的情感聯(lián)系;只要這4個元素共存,社區(qū)或共同體既可以從關系條件定義,也可以從地域條件去定義(Almgren ,2000)。在我看來,這些爭議顯示了很難否定地域邊界性仍然是社區(qū)或共同體的重要條件。即便在社區(qū)脫域性較強的美國城市也是如此。一項新的關于美國50個城市公社的實證研究成果,雖然指出美國的城市共同體十分依賴于道德秩序與文化的共享性,甚至提出這可能是最直接作用于共同體形成的機制,但是也承認對自然空間、權力關系、高收益要求等機制的團體認同,與Gemeinschaft積極關聯(lián),兩類因素同時發(fā)揮作用(Vaisey,2007)。至于共同體研究中的社區(qū)研究(community study),則一直聚集在三個確定的地方類型上:鄉(xiāng)村或村落社區(qū)、小鎮(zhèn),以及工人階級社區(qū);從中形成的關于傳統(tǒng)社區(qū)自然狀態(tài)的概念,對共同體研究起支撐作用(Day ,2006:27)。弗雷澤研究了社區(qū)研究的傳統(tǒng)后,甚至斷言社會學家們是把社區(qū)視為一個居民定居的位置、一個由多元關系的密集性網(wǎng)格組成的穩(wěn)定社會結構、以及高度相關的對外邊界(Frazer ,1999:67)]而地區(qū)、城市、都市、國家等完全不借助Gemeinschaft或community 的概念也能獲得清楚的內(nèi)涵與外延;更主要的是因為,社區(qū)或共同體的地域性與其說是一種保守陳舊,不如說顯示了人仍然是“劃分邊界的動物”(Day ,2006:2)。就社區(qū)邊界劃分而言,它本身不是目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藉此才能有效支持經(jīng)濟互助與情感聯(lián)系。即,一方面,劃分社區(qū)邊界通常是便于滿足邊界內(nèi)(特別是面對面交往的)成員間的非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互助與交換。
在歷史上,雖然絕大部分的共同體主要不是以營利為取向的經(jīng)濟團體,但一般都具有經(jīng)濟功能,內(nèi)部通常也存在著分工和交換,只是這種分工和交換一般不是純經(jīng)濟,至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①[經(jīng)濟史家已經(jīng)指出,當斯密強調(diào)新時代中分工與交換的效用,通過市場交換帶來社會各階層普遍富裕時,他混淆了一個問題。分工與交換也存在于共同體之中,這種分工并不一定需要市場經(jīng)濟中的交換,交換作為人與人之間交換各自的剩余物品的行為,也未必直接與分工相關。人和動物都擁有不依靠貨幣媒介便可合作生存的群體性生存形態(tài),即共同體的生存形態(tài)。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分工與交換是從共同體之間交換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馬克思會說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山口重克,2007:91-92、18、45)
在市場經(jīng)濟嵌入社會的情況下,市場經(jīng)濟因素主要在共同體之間發(fā)揮作用,可能也會在共同體內(nèi)部發(fā)揮補充作用,而共同體的規(guī)則被用于彌補市場經(jīng)濟無法滿足共同體的群集生活的那部分內(nèi)容。②[因此,一些善良的經(jīng)濟學家希望實現(xiàn)與共同體相協(xié)調(diào)的市場經(jīng)濟的繁榮,希望共同體之間能夠通過和平的市場經(jīng)濟相互交流,用交換規(guī)則建立共同體之間的聯(lián)系(山口重克,2007:84)。這種愿望既表明共同體之間可能需要市場聯(lián)系并因此聯(lián)結成更大的社會結合體(例如區(qū)域社會、國家管理下的社會等等),但是共同體本身不是基于市場經(jīng)濟實現(xiàn)互相幫助、滿足需求的,也并非所有的現(xiàn)代社會結合體都是共同體;同時,它也表明所謂社區(qū)共同體衰退是獲得現(xiàn)代社會的自由與機會的代價(Little,2002:8)可能是魯莽之論]當然,社區(qū)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的命運,也由此相當程度地取決于它的成員間非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互助與交換是否仍然被需要,取決于這個系統(tǒng)與市場交換特別是社區(qū)外市場交換能否銜接、如何銜接。另一方面,社區(qū)作為小型、緊密的地方性共同體被需要,也是在情感和社會認知意義上的——鮑曼甚至把它概括為人們尋找確定性的需要(鮑曼,2007)。社會學研究通常承認,面對面日常互動與非面對面互動的效果完全不同,熟悉的人群中產(chǎn)生的道德約束與情感聯(lián)系的強度與性質(zhì)也完全不同于陌生人群。③[所以,敏感的社會學家發(fā)現(xiàn)了兩個有趣的現(xiàn)象。其一、在現(xiàn)代都市,所謂異質(zhì)化的人們在個人行為方面其實很相似,具有行為上的“同質(zhì)”化,而沒有什么當?shù)匦浴R牢謧惖挠^察,“可以肯定,社區(qū)之間在價值觀、準則、主導利益、方式和其他文化方面有區(qū)別。但如果觀察一個人在繁華街道角落、超市、或自己家、或體育事件的公開行為,他會很難知道這人是在匹茲堡,而不是圣路易斯;是在布利奇波特而不是洛克蘭;在亞特蘭大而不是丹佛”(Warren,1978:429)。其二、在交往行為上,陌生人之間(城市、社會)與熟人之間(社區(qū))是不同的。鮑曼說:“塞特納??認為,‘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讓我補充一點,這意思是說??陌生人以適合于陌生人的方式相遇;陌生人之間的相遇不同于親戚、朋友或熟人之間的邂逅相遇——相比而言,它是一個不合適的相遇。在陌生人之間的相遇中,不會去重新找到他們最后相見的地方;在兩次相遇的間歇期間,他們談不上痛苦,也談不上高興,更不會產(chǎn)生任何共同的回憶:對任何東西都不會產(chǎn)生回想,也沒有任何東西需要在當前的邂逅過程中去加以遵循。陌生人的相遇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沒有將來的事情(它被認為是,并被相信是一個擺脫了將來的事性),是一段非確切的‘不會持續(xù)下去的往事,是一個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在到場和它持續(xù)的那個時間里,它就會被徹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著有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將未了之事推遲到另一次相遇中??在他們相遇之時,沒有嘗試和錯誤的余地,無法吸取錯誤的教訓,也沒有另一次嘗試的機會和希望。”結果,都市生活只要求有一個相當特殊和熟練的技巧、禮儀客套規(guī)則(鮑曼,2002:147-148)。
沃斯也提出:在人口密度高、異質(zhì)性強的城市社區(qū),人和人的接觸表面化或片面化,初級的人群關系變淡,個人容易感到孤獨(Wirth ,1938)。這些批評本質(zhì)上支持一種觀念:社會是一種存在于廣泛合作關系中的綜合實在,所以既是外在的,又是內(nèi)在于個人的(梅勒,2009:15-16);共同體則既是一種合作層次,是社會子層合作的形成,更是體現(xiàn)了一種需要緊密合作的情感。所以,地方性的共同體很難說是過時的,雖然它在所謂傳統(tǒng)社會中更為常見]對于個體而言,社區(qū)共同體邊界里面對面互動的、相互熟悉的人群,不僅常常是個體認知社會的基本場域、基本情景區(qū),而且是個體在社會中滿足與否的基本定位點、基本參照對象。例如,個體滿足與否的內(nèi)心感受、社會生活評價,首先或經(jīng)常是在熟悉的人群中比較出來的,人群愈熟悉愈有可比較性和可持續(xù)比較效度,愈不熟悉愈只有即時或暫時的比較效度,甚至不被個體在意;或者說,愈是被個體所熟悉的人群,愈是個體關于社會和自我的定位點,愈是個體關于自我與社會的經(jīng)驗與感受的“不會消失的見證人”(鮑曼,2007:52)。這是社區(qū)作為面對面交往的地方性共同體隱蔽地嵌入個體意識的心理基礎。①[所以,梅勒說社會情感剌激存在于最平常的日常互動中而產(chǎn)生“初級社會性”(梅勒,2009:162)。而布迪厄所謂慣習(各種不言而喻的信念、知識)作為一個持續(xù)的、可轉化的秉性系統(tǒng),也是首先就存在于社區(qū)為人們提供的日常生活圈。社區(qū)就這樣不受人注意地嵌入到個體意識中。依威爾金森等人的觀察,社區(qū)顯然是個體人格成長的主要影響要素,它是個體與社會聯(lián)系之所,是家庭之外的社會體驗的最初領域,是直接表達人走向聯(lián)合的舞臺,可以培養(yǎng)獨特的集體責任態(tài)度(Wilkinson ,1979);也是人滿足需求,特別是避免社會孤獨感的基石(Greisman ,1980)。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滕尼斯一開始指出Gemeinschaft體現(xiàn)了人們的自然的、本質(zhì)意志(natural will ,即基于感情與信任的結合),而Gesellschaft體現(xiàn)理性選擇意志(rational will,即基于彼此利益或契約的聯(lián)合)時,他至少是覺察到人的社會感覺的定位標度是有地方性的,社區(qū)作為地方性共同體則是人們感知社會與自我,以及做出滿意與否評價的基本參照系統(tǒng)之一。共同體的實質(zhì)性理論所強調(diào)的共享道德感及其激發(fā)的歸屬感,可能的確是社區(qū)共同體的特征和基礎,但是,這不意味著人們的道德感、歸屬感與地方感(特別是面對面交往之地)不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第二,社區(qū)作為地方性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和基本境遇,一方面表明村落共同體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支撐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例如國家的行政村體制安排)在現(xiàn)代可能松動甚至剝離,但它作為社區(qū)共同體仍然是正常的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資源,因此,聽任或助推市場力量掃蕩村落共同體,并不是正常的社會要求和社會現(xiàn)象。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村落共同體要在現(xiàn)代社會保持活力,不僅需要謀求社區(qū)內(nèi)發(fā)展,更需要恰當?shù)赝黄频乩磉吔纾ㄟ^謀求社區(qū)外聯(lián)系以及社區(qū)外力量對社區(qū)的介入而發(fā)展社區(qū)(Summers,1986),而不是謀求使村落逃避復雜的變遷力量,更不能指望把社會重新“部落化”為一個個孤立的、自我維系的單位(Boissenvain,1975)。但是,由于村落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面臨空前復雜的推壓力量,村落共同體究竟可以以何種方式、途徑聯(lián)系社區(qū)外力量,究竟趨向存留、新生還是衰亡,客觀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與其他共同體特別是現(xiàn)代各種職業(yè)團體相比,支持傳統(tǒng)村落共同體存在的特別基礎通常來自兩方面。其一,經(jīng)濟方面,農(nóng)耕技術經(jīng)濟條件不僅支持家庭農(nóng)業(yè),而且導致不易分割農(nóng)戶家庭財產(chǎn),社會通常也支持家庭作為共同消費之地。農(nóng)村家庭的穩(wěn)固存在不僅造成經(jīng)濟與社區(qū)不分離的狀況,而且一般會支持鄰人關系及村落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并強化村落共同感。一如韋伯所析:“家是一種滿足一般日用的財貨需求與勞動需求的共同體。在自給自足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中,遇到緊急的狀態(tài),極端的匱乏與危機而有非常需求時,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必需仰賴超越家共同體之上的共同體行動,亦即‘鄰人’(Nachbarschaft )。”①[“所謂‘鄰人’,我們所指的并不單只是因為農(nóng)村聚落的鄰居關系,而形成的那種‘原始的’形式,而是所有因空間上的接近,換言之,基于長期或暫時的居住或停留而形成近鄰關系,從而產(chǎn)生出一種長期慢性或曇花一現(xiàn)的共同利害關系??以此,按聚居方式之不同,‘鄰人共同體’在表面上看來自然極為形形色色,諸如:散居的農(nóng)家、村落、城市街坊或‘貧民窟’”(韋伯,2004:261-262)。當然,村落共同體存在并不表示共同體行動總是通則,比起家共同體的經(jīng)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總是不密集連貫、范圍不太確定(山口重克,2007:15、20)]其二,出于特定政治統(tǒng)治或治理體系的需要,政治權力通常也會支持或強化村落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單位,甚至以政治和行政力量認可或劃定村落共同體的地理邊界。正因如此,傳統(tǒng)村落共同體常遭詬病的特別問題也有相應的兩方面。其一,地域邊界明顯。村落共同體有可能“不借助社會其他成分的幫助而獨立進行其自身的再生產(chǎn),即通過自身的手段(內(nèi)部社會化)最終把下一代培養(yǎng)成與自己相似的成年人,從而使社區(qū)結構及其文化以這種方式世代存續(xù)。作為傳統(tǒng)社會的組成部分,這種社區(qū)只是它所組成的更廣泛的社會一個較小的變異體,可以在更小的范圍內(nèi)做那個更大的單位即社會能夠做的一切”。“這種社區(qū)具有強烈的地域認同感和忠誠感”(馮鋼,2002),但是既存生活方式的重復再生產(chǎn)(Day ,2006:28)也會形成鮑曼所譏剌的嚴格區(qū)分你我、限制自由入出的共同體邊界。其二,如韋伯(2004:234-245)略帶譏諷的描述:共同體可能發(fā)展為獨占體,如果解體則權益落于私有制。所以,共同體有可能向擴張為更大的社會結合體的方向發(fā)展,也可能往獨占體方向發(fā)展。由此,村落共同體在現(xiàn)代社會能否繼續(xù)存在并發(fā)揮社會團結作用的關鍵,也就在于是否存在著社區(qū)共同體聯(lián)結社會的可能性,即在抽象意義上說取決于村落共同體關系能否被發(fā)展成韋伯所說的“合理性的‘結合體關系’”。①[韋伯還指出,共同體成員專門資格規(guī)定易招致有些人一味追求會員資格可資利用的門路;近似的共同體在互相爭取成員時,即使基本上非經(jīng)濟性的共同體也有意識許諾具體的經(jīng)濟利益(韋伯,2004:243)。不過,這主要不是針對鄰人共同體與村落共同體]具體說,取決于:其一,向內(nèi)能否適當?shù)貜娀迓涔餐w的經(jīng)濟規(guī)制團體的性質(zhì)和功能,有效地把家庭共同體置基于經(jīng)濟上互助互補,而不僅是文化上的手足之情。其二,向外能否在現(xiàn)代職業(yè)團體發(fā)揮越來越大的社會整合作用的情況下,找到打破村落邊界,既鏈合外部社會又保持村落共同體團結紐帶的原則與途徑,把村落共同體發(fā)展成為社會結合體的一部分。
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沒有村落共同體與社會聯(lián)接的可能性,而是市場和國家力量同時介入農(nóng)村后,村落共同體面臨的推拉力量空前復雜,從而面臨著聯(lián)結社會的多重可能性。所謂“推拉力量”,不僅是經(jīng)濟性質(zhì)的——例如劉易斯假設的農(nóng)村為緩解人地矛盾、轉移剩余勞動力而產(chǎn)生的推力,以及資本與現(xiàn)代部門解決勞力不足而產(chǎn)生的拉力(劉易斯,1989;黃宏偉,2005),同時也是社會性的。韋伯曾提出一個關于家共同體解體的解釋:“在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促使緊密一體的家權力趨向衰微的內(nèi)在動因與外在動因不斷增加。自內(nèi)而起的解體動因在于:能力與需求的開始與分化,而這與經(jīng)濟手段在量方面的增加相關聯(lián)。隨著生活可能性的多樣化,個人愈來愈不能忍受共同體先前所硬性規(guī)定的、未分化的生活形態(tài),從而愈來愈傾向于以一己之力來形塑自己的生活,并且自由享受單憑個人能力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成果。外在的解體因素則來自于競爭性社會組織的介入:例如國庫有意要更加密集地榨取個人的賦稅能力”。前一種力量,即個人主義營利方式一旦成立、個人主義觀念一旦形成,“將自己委身于一個大型的共產(chǎn)家計里的誘因,委實愈來愈少”(韋伯,2004:281-282),這可以被視為家庭共同體瓦解的內(nèi)推力量,后一種力量則可以稱為共同體瓦解的外拉力量。顯然,韋伯所言并不僅僅適用于觀察家庭共同體,也適用于觀察社區(qū)共同體之外的種種社會經(jīng)營所產(chǎn)生的村落共同體的分解力量。另一方面,通常還同時存在著抑制村落共同體分散的“反向推拉力量”:其一,存在著把個人推向村落共同體的力量。除了農(nóng)村居民可能有鄉(xiāng)土歸屬感,可能通過合作社進入市場,以及特定國家在政治上選擇村莊為基層治理單位并支持村莊自治等等,小農(nóng)個體在城市和市場上的經(jīng)常受挫也會迫使他們轉而依賴傳統(tǒng)的村落共同體互助。例如,一些關于東、中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化的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計劃經(jīng)濟與市場經(jīng)濟混雜時期產(chǎn)生的新的不平等、階層化,使農(nóng)村居民產(chǎn)生心理痛苦,被迫發(fā)展適應性的家庭經(jīng)營策略(B rown Kulcsar,2000,2001)。農(nóng)民家庭面臨矛盾的選擇:一是選擇發(fā)展更密集的社會性網(wǎng)絡,農(nóng)村居民個體和家庭將更少聯(lián)系對他們達到市場目標沒有直接幫助的人,結果是更少卷入所居住的社區(qū)。另一個選擇是更傾向于發(fā)展社區(qū)內(nèi)的非正式社會互助網(wǎng)絡,去應對混亂的經(jīng)濟和社會保障系統(tǒng)的缺失,個人與家庭都因此更加依賴鄰居互助,結果更加緊固了社區(qū)紐帶而疏離了社會紐帶(O‘Brien et al.,2005)。其二,還存在著出于經(jīng)濟、政治甚至文化和人道的力量和目的,試圖平衡城鄉(xiāng)發(fā)展,振興鄉(xiāng)村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社區(qū)共同體,改變傳統(tǒng)鄉(xiāng)村精英把持權力的格局,增強鄉(xiāng)村大眾的權力,并使村落共同體鏈接社會以形成社會結合體的拉力。例如從20世紀后半期起,拉美和非洲的地權運動,亞洲的小農(nóng)組織,北美和歐洲的改革活動與社區(qū)激活,歐洲、北美與澳洲的激進農(nóng)場主團體,鄉(xiāng)村認同運動與鄉(xiāng)村社區(qū)發(fā)展運動(包括本土居民運動、回到土地自愿者和環(huán)境維護者對鄉(xiāng)村調(diào)整的抗議等等),都為積極進行鄉(xiāng)村社會重建的新鄉(xiāng)村社會運動的動員創(chuàng)造了空間。雖然這些運動在鄉(xiāng)村社區(qū)與社會的關系目標上存在某些不同取向,但要求小農(nóng)的土地權利,保護農(nóng)業(yè)的傳統(tǒng)方式并反對新自由主義土地改革、經(jīng)濟自由化和農(nóng)產(chǎn)品跨國企業(yè)行為,則是其共同取向(Woods ,2008)——在我看來都是反對用市場規(guī)則聯(lián)結鄉(xiāng)村與社會。
以上四個方向力量的存在,客觀上造成村落共同體有四種聯(lián)結社會的可能性。通常,既要打破共同體邊界又要保持小型、地方共同體規(guī)則是極其困難的。莫爾在《烏托邦》中曾表達過天才而憂郁的預見:一個烏托邦即使全力抑制公民間差異性而達到平等和一致性,仍然面臨外部世界的威脅,除非全世界都通行烏托邦規(guī)則。因此,莫爾為烏托邦設想了一項重大工程:掘開海溝把與大陸聯(lián)結的烏托邦半島變?yōu)闉跬邪詈u。該工程絕不只為了便利烏托邦的軍事防衛(wèi),更是為了把烏托邦與外部世界的必要交換減少到最小、最主動的程度,以便在不能把全世界都變成烏托邦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保護作為小型共同體的烏托邦——這恐怕是馬克思關于共產(chǎn)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單獨取勝論斷的思想來源。這里如果借用莫爾的烏托邦文學底本,把廣闊社會比作茫茫大陸,把弱小而相對封閉的村落共同體視如小型島嶼,那么可以說:村落共同體與社會的聯(lián)系原來就以共同體成員不認識或不方便的自然形式存在(一如大海把島嶼和內(nèi)陸聯(lián)結一起),而人們自覺建立與發(fā)展兩者間的聯(lián)系則猶如設法過海。莫爾設計的烏托邦掘海工程,把聯(lián)結大陸的半島再變回島嶼,島民與世界聯(lián)系只能通過船只,實際上就是第一種過海可能性與策略選擇。在現(xiàn)代社會,它可能表現(xiàn)為要求簡單強化村落共同體的主張和行動,屬于逆市場化、逆城市化的方式。第二種過海方式,是指原本處在島嶼的居民(村落共同體成員)自然地以船過海,與其他島嶼和大陸作各種必要交換,彼此關系相對不密切不方便但可以取其所需,其中的經(jīng)濟交換可能是非市場交換性質(zhì)也可能是市場經(jīng)濟性質(zhì)的。某些國家和社會選擇聽任鄉(xiāng)村地區(qū)和村落共同體自生自滅,大體屬于這一類方式。第三種過海方式與烏托邦掘海工程逆向,即實施填海工程,人為建立島嶼與島嶼、島嶼與大陸的陸行聯(lián)系,把所有島嶼最終都變?yōu)殛懙亍L詈9こ痰脑靸r昂貴;工程完成后,島民從此可以自如陸行,但是走遠了走久了可能不再回來,或者想回來而迷路。在現(xiàn)代社會,純粹以市場經(jīng)濟方式掃蕩村落共同體,從而滿足市場力量對于自由勞動力和土地的覬覦,屬于典型的社會填海工程。第四種過海方式,則是本文后面要討論的建立恰當?shù)摹⒅荚跍p輕或消除城鄉(xiāng)社會不平等的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如同造跨海大橋,既可以最小環(huán)境代價和小農(nóng)權益最大化的方式建立起島嶼間、陸島間的快捷交通,又保持島嶼生活的可選擇性;跨海大橋還需有不同于普遍橋梁的形制設計——包括在公民個體間友善原則之上推動共同體之間的友善政治倫理。
面對過海比喻或“過海理論”所表述的四種可能性,國家以及包括村落共同體在內(nèi)的社會力量究竟選擇哪一種,取決于人們爭取什么,取決于人們采取何種社會原則、把哪種社會構成視為正常。對于這個問題,公共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理應積極介入。
三、村落共同體與公民社會:公共社會學的關心
關心公民社會建設的公共社會學實際上也面臨一個重大問題:村落共同體作為地方性共同體究竟是不是公民社會的敵人?村落共同體在當代社會有多大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它與公民社會的關聯(lián)。
倡言公共社會學的布絡維本人并沒有細致觸及公民社會究竟是基于個體的個人主義理性聚集,還是基于公民社群或團體的價值與利益共享,抑或是公民個體、公民團體與共同體的結合——這在他也許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共同體或社區(qū)從古典社會學開始就被用來解釋社會如何團結在一起,是什么賦予集體或團體以單位和區(qū)分,以及社會紐帶被強化或被社會變遷社會發(fā)展所規(guī)定等等。因此,“社區(qū)”,特別是肯定“社區(qū)”存在意義的研究代表的是一種關于團體及其區(qū)別于孤立狀態(tài)或個人主義的重要討論(Day ,2006:2、24-25),即是關于社會構成的非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討論;而個人主義的純粹競爭性聚合會被傾向于視為失序狀態(tài)或“失范”。不過,政治社會學、社會學所設想的公民社會的確存在著兩種甚至更多的可能性。在自由主義關于合理的公民社會的設想中,個體作為理性個體、私人進入公民社會,①[社會學的社群主義認為共同體或社群是兩種要素的聯(lián)合:(A )在個人組成的團體中間的一種充滿影響力的關系網(wǎng)絡,這些關系經(jīng)常交叉并且互相強化,而不只是一對一或個人關系的鏈接。(B )對于共享價值、規(guī)范、意義的承諾,以及共享歷史和對特別文化的認同(Etzioni,2000)]一如哈貝馬斯早期所強調(diào)的,理想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是由理性的私人組成,公共領域作為市民社會銜接國家活動的區(qū)域和部分,本身仍屬于私人領域的組成部分(哈貝馬斯,1999:2、31、41、59、96;Warren,1995:171-172)。因此,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在根本上沒有理由重視共同體,更沒有理由尊重村落共同體。另一類政治社會學則把共同體視為一群人,在表達認同感時吸收了一組相同的符號資源;它不僅是與認同的其他形式相匹敵的一種認同形式,還是塑造認同的一種共同的手段。所謂共同體是通過劃定邊界和管轄成員來發(fā)揮功能,邊界則是通過相似性和差異性的二重數(shù)軸劃定的。身處共同體的體驗就是以一種方式闡釋或解釋社會世界,盡管這種方式與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卻可以與之一致(Cohen ,1985;納什、斯科特,2007:297)。因此,既然國家在現(xiàn)代仍不可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控制社會的每一個人,那么要把社會凝聚、整合起來,“社區(qū)發(fā)展”就是將社會控制下移到一個個自治社區(qū)手中的“分權方案”,其目標是通過社會基層組織的自治,來調(diào)整政府與民間的關系,并實現(xiàn)社會整合(馮鋼,2002)。
這種分歧表明,地方性共同體是否被視為公民社會的敵人,首先取決于公民社會是什么性質(zhì)的,或者說,取決于公民社會應該被視為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之上還是方法論社群主義之上。從前一個立場說,村落共同體可能是公民社會的潛在敵人。從后一立場看,村落共同體不是公民社會的敵人,而是一個友善的公民社會的組織支柱。例如,1990年發(fā)布“積極的社群主義的宣言”,并將泰勒(Charles Taylor)、桑德爾(Michael Sandel)、沃澤爾(MichaelWalzer )的政治哲學的社群主義拓展為社會學流派和社會運動的澤奧尼,曾這樣概括兩種立場的區(qū)別:社會哲學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核心預設是必須共享利益;自由主義的核心預設則是人們的考慮無論對錯,都有權做出個人決定,社會安排與公共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是需要的,但是不應該被共享價值所驅使,只能由個人卷入的自愿性安排和契約所驅使并反映他們的價值和志趣。社群主義認為社會制度與政治受傳統(tǒng),因而受代代相傳的價值的影響,它通過非理性的過程,特別是內(nèi)化過程而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并且被諸如說服、宗教或政治教化、領導,以及道德對話等過程所改變。由此,社群主義還強調(diào)人們對其家庭、親屬、社區(qū)以及社會有一種特殊的道德責任,因此,它雖不拒斥基本的自由主義理想及其功績,但是鼓勵一種責任倫理,一個好社會被認為是基于小心翼翼達成的自由與社會秩序之間、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特性(倫理的、種族的、共同體的)與全社會價值及聯(lián)合之間的平衡。而自由主義則強調(diào)但凡個體都有普遍權利,可以忽略個體的特殊的成員身份——在此意義上所謂社會的觀念甚至是虛構的。
澤奧尼強調(diào),社會學的社群主義見解既是經(jīng)驗性的也是規(guī)范性的,比起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更具經(jīng)驗依據(jù)。它觀察到,人生來與動物類似而非自由主義所謂人生而道德,但是在社會制度下經(jīng)過適當?shù)膬r值內(nèi)化與強化,人能增進品德。作為一個好社會基石的道德基礎則是由四個社會形式塑造的,即家庭、學校、社區(qū),以及許多社區(qū)組成的社區(qū)(the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這四個核心要素如同大盒套小盒的中國盒子:嬰兒出生在家庭中,慢慢接受價值、發(fā)生道德自我;學校在孩子變大時進一步發(fā)展他們的道德自我,或者矯正其特性;社區(qū)或社群則通過強化其成員特征而加固其道德基礎,不至于使個人失去對價值的承諾。社區(qū)中的道德聲音作為他人的非正式贊同會形成一個非正式影響的關系網(wǎng)絡,比國家力量更能為社會秩序提供道德基礎;社區(qū)或社群愈弱(例如人口流動量愈大、共享核心價值愈少、異質(zhì)性愈高),則社會網(wǎng)絡愈疏,道德聲音愈稀。當然,社群具有邊界性,社群之間可能發(fā)生沖突,因此社群之上、由許多社區(qū)或社群所組成的社群——即社會——就是重要的。基于這個經(jīng)驗基礎,社會學的社群主義堅持不能視社會由千百萬的個體所組成,而應視之為復合團體(aspluralism with inunity),其中的亞文化與地方單位并不是對社會整合的威脅,只要社會的核心共享價值和制度受到尊重;自由與社會秩序、自我與共同體的關系也不是零和的,社群中的個體比孤立的個體更加理性、有效率(但是如果社會壓力持續(xù)達到高水平,它會破壞自我的發(fā)展與表達)。
社會學的社群主義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強調(diào)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or civil society),即各種公民結社制度有助于個體互助以滿足其社會需要,可以部分地肩負起原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福利責任;另一方面則強調(diào)公民社會雖然好但是不夠充分,因為公民社會在許多事務上更傾向于道德中立,而不是關心價值自身固有的品性,以及如何把它們變成公民的需要并使他們成為公民社會更有效的成員(例如更加批判性地思考),為此,一個好社會要追求發(fā)揚實質(zhì)性的核心價值,而且不能不區(qū)分對待公民團體,即認為其中某些社會團體和活動更有品德(Etzioni,2000)。
澤奧尼發(fā)起的社會學的社群主義運動并不專門、大量地涉及村落共同體與公民社會的關系,但是它與自由主義的爭辯還是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村落共同體與公民社會的兩個層面的關聯(lián)。
第一,如果在社會學的社群主義立場上做出拓展,則不難發(fā)現(xiàn):1.存在著非城居的國民是否應該和如何組成公民社會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面對既存的村落共同體、農(nóng)村居民與公民社會的關系與通道問題。甚至,問題首先不是村落共同體與農(nóng)村居民是不是公民社會的敵人或拖累,而是農(nóng)村居民有權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2.類似于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觀察到的19世紀美國廣泛存在的社團、社區(qū)組織等自治團體不僅有助于抵擋國家暴政,而且有助于公民在參與熟悉的地方性公共事務過程中自然地培養(yǎng)公共熱情與公益能力,成為合格的公民;社會學的社群主義也強調(diào)好的公民社會是社群的復合體,好的地方性共同體是好社會的基礎,身處這類共同體中的公民會由于共享價值、文化紐帶、互助互惠而更富于合作、理性和效率。這類經(jīng)驗觀察,說到底是在規(guī)范意義上主張公民社會中公民與公民之間不能只存在計算私利、斤斤計較的經(jīng)濟關系,只在公共領域中發(fā)展你爭我斗的權力關系,而要保持阿倫特(HannahArendt——臺灣譯鄂蘭)反復致意的友善、鄉(xiāng)誼(鄂蘭,2006:31-32),以免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淪為公民的合法爭吵場。在此意義上說,一個與社會核心價值、制度保持一致的村落共同體,正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而且好的村落共同體正是農(nóng)村公民既培養(yǎng)公共關心,同時保持鄉(xiāng)誼、保護公民間友善的特別溫床。3.與“過海理論”相一致,在實踐上由于公民社會類型、村落共同體前景都存在著不確定性,村落共同體與公民社會的關系與通道完全可能趨向不同方向。例如,聽任市場力量自行作為,村落共同體有可能被瓦解成為殘余的私人的聚居鏈接,遑論成為公民社會的鄉(xiāng)村形態(tài);單純推進基于方法論個人主義而設計的選舉政治、鄉(xiāng)村自治,村落共同體成員也有可能加速趨向原子化公民、或政治利益小宗派,遑論確立農(nóng)村與城市的公民政治聯(lián)系,以及基于農(nóng)村的經(jīng)驗和政治實踐達致公民社會。
第二,社區(qū)雖然被視為新進步主義的基石之一(Day ,2006:15),共同體精神雖然被社會學的社群主義反復提議,甚至被期望為抵制自由市場經(jīng)濟學及其自由主義哲學的社會基石,存在于家庭和小型社區(qū)內(nèi)的互惠被認為需要擴展到目前受經(jīng)濟思潮主導的國家關系和全球關系中;但是,社群主義的公民社會并非沒有疑問。誠如人們所批評的,公民社會并不盡善,某些社團、社群甚至是反社會核心價值和制度的,社區(qū)或社群并非解決現(xiàn)代社會利益宗派化的天然解毒劑。因此,公民社會及其理論甚至需要祛魅。就村落共同體而言,所謂祛魅,是指它能否成為一個好的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不僅取決于村落共同體內(nèi)部能否維系良好的公民團結,而且取決于村落共同體能否處理好與其他共同體的關系,由共同體內(nèi)部的公民鄉(xiāng)誼發(fā)展出共同體之間的友善,共同維護核心共享價值與制度,并避免形成社會組織間的宗派爭斗;取決于能否與一個好的公民社會形成良好聯(lián)結,并與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制度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村落共同體要成為公民社會的構成,需要邁出兩大步:基于村落共同體的資源,恰當?shù)赜柧氜r(nóng)村居民的公共關心和處置公共事務的能力,是為第一步;解決村落共同體與其他共同體及社會的政治鏈合,是為第二步。但是,爭取這種關系與前景,首先需要以各種共同體的社會、政治平等和經(jīng)濟互補為條件。如果村落共同體還被置于城鄉(xiāng)二元化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國家福利框架之中,城鄉(xiāng)兩種社區(qū)還處在極度的社會不平等之中,村落共同體作為公民社會的積極構成只是奢談。顯然,改變這種狀態(tài),有待于積極的國家干預。
四、十字路口的中國村落共同體與城鄉(xiāng)銜接:政策社會學的問題
英語世界的鄉(xiāng)村社會學把鄉(xiāng)村聚落分為小村落(hamlet )、村落(village)、集鎮(zhèn)(township )、城鎮(zhèn)(town )等。小村落通常是沒有教堂的小村子。村落比之于小村落,規(guī)模大(從數(shù)十戶到數(shù)百戶)還屬次要特征,最重要的是它有教堂及其他公共性的中心。這里所討論的中國村落,確切說是指行政村,即是中國當代政治、社會進程中產(chǎn)生的一種“Village ”(自然村大體對應于hamlet)。這種行政村算不算共同體,是什么意義上的共同體,在概念上顯然有爭議。在鄉(xiāng)村社會學領域,197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者曾從社會史角度特別有力地論證過,與“社會”形成對照的傳統(tǒng)村莊共同體或社區(qū)只存在于概念和假定上,更多的是某種民俗記憶,鄉(xiāng)村社區(qū)一直被卷入社會發(fā)展進程(Newby ,1987:78)。
有些關于鄉(xiāng)村社區(qū)性質(zhì)、功能、特征的經(jīng)典描述與定義(諸如把社區(qū)描述為靜態(tài)的、傳統(tǒng)的、團結的與邊界固定的),還被批評為缺乏歷史分析尺度,以至于把一時現(xiàn)象視為永久特性,例如吉本(Gibbon ,1973)等人指出1940年代艾瑞森柏格和肯波所描述和解釋的愛爾蘭西南部鄉(xiāng)村社區(qū)的團結、穩(wěn)定、互助、和諧等等特征(Arensberg Kimball ,1940),有很多實際上是受1840年代馬鈴薯歉收影響的結果。批評者們雖然多少承認社區(qū)具有團結和整合功能,但是更強調(diào)農(nóng)村社區(qū)充滿了變遷、分化、矛盾而具有復雜的模式。本文同意這類批評,因為本來就很少存在完全吻合gemeinschaft概念的共同體,實存的中國村落共同體同樣也處在雷德菲德所說的連續(xù)變遷序列中的某個位置。此外,1940到1970年代日本學者曾基于同樣的滿鐵調(diào)查材料,專門就中國村落能否被稱為共同體展開論戰(zhàn)。持否定意見者認為中國村落缺乏共同體應有的邊界、共有財產(chǎn)、村落觀念,而持肯定意見者則強調(diào)有這些證據(jù)(李國慶,2005;黃宗智,2000b:26-27)。論戰(zhàn)的“核心實質(zhì)”曾被歸為“是家優(yōu)先還是村優(yōu)先的問題”(李國慶,2005)。實際上,家優(yōu)先作為農(nóng)村常態(tài)一般并不妨礙村落共同體的產(chǎn)生與維系,關鍵是中國同一時期不同地方的村落共同體受國家、市場和內(nèi)部三種壓力的不同交替作用,會導致共同體的產(chǎn)生過程、形式、機制、松緊度有所不同,這才是日本學者使用同一批材料而得出不同意見的根源之一。通常,只在理論上存在著村落共同體完全由社區(qū)內(nèi)部力量自發(fā)形構的可能性,實際上國家力量、市場力量總是參與,影響甚至決定村落共同體的邊界、機制和功能。①[以美國為例,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關于鄉(xiāng)村與城市的界定,依賴于聯(lián)邦政府的兩個系統(tǒng)關于城鄉(xiāng)的劃分。美國人口普查辦公室依照人口密度劃分城市與鄉(xiāng)村地區(qū),根據(jù)2000年人口普查,有近500萬鄉(xiāng)村人口生活在2500人規(guī)模以下的社區(qū)中。而管理與預算部門則以都市區(qū)與非都市區(qū)表示城市、鄉(xiāng)村的整合角度,并且對鄉(xiāng)村使用了15個以上的不同角度的界定(例如從通訊負擔角度把5000人以下居住區(qū)視為鄉(xiāng)村,而從供電角度劃分鄉(xiāng)村的標準,2000年前為1500人以下,2000年改為2500人以下,等等)。美國政府建立這種地方標識通常出于管理目的:決定哪些地方適合特定的政府項目,即相應的鄉(xiāng)村界定都服務于政策目標(Flora Flora,2008:7-9、12-13)]因此,清末民初以來國家影響、甚至劃分村落邊界,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取消了中國的村落共同體(黃宗智,2000b:24-28、312-314,2000b :148-159),而是意味著村落共同體的邊界、方式、功能以及自治(如果有的話)受到共同體之外力量的形塑,以便適合國家選擇的鄉(xiāng)村治理模式。
1980年代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結束、實施政社分離而出現(xiàn)的80多萬個行政村(現(xiàn)減并為60多萬個),顯然既具有國家行政規(guī)定的色彩,同時也有農(nóng)村自然聚落的基礎。它基本上都在人民公社體制中的大隊一級設置,與公社體制相比,一方面是延續(xù)了1949年以來,特別是集體化以來國家在農(nóng)村以集體組織取代其他村落共同體(例如宗族共同體)的政治努力;另一方面則把農(nóng)村集體的核心層面從公社下降一級、從生產(chǎn)隊上提一級。這個體制推出之初,作為顯性規(guī)制,它使原來大隊一級的村集體被確認為村落首要的、首級的共同體,其他合作體(如原生產(chǎn)隊、后來的村民小組)為次級,家庭為基本共同體。它意味著國家承認農(nóng)村集體(或共同體)是有地方性的,它涉及特定的居民、文化和環(huán)境的關系,與國家設置的地方邊界可能很不一致,至少公社作為集體過大,政府也無力把公社與城市社區(qū)或單位一樣整合納入國家政治、經(jīng)濟和福利體系;同時承認從高級社以來漸次形成的自然村聯(lián)合的大隊已經(jīng)是被農(nóng)戶廣泛認同的村集體,要求它在國家撤出對農(nóng)村經(jīng)濟和社會直接治理之后作為農(nóng)村社區(qū)共同體擔當村落公共供給的主要責任(毛丹,1998)。作為隱性規(guī)制,實施政社分離、行政村制度,并且與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相配置,是在激勵農(nóng)戶單位的生產(chǎn)積極性的同時,把農(nóng)村基層公共供給的負擔卸給行政村,以便繼續(xù)保持國家供給和發(fā)展城市的能力。它意味著更多地增強了農(nóng)戶的自主性,放松了對農(nóng)民以勞動力個體進入市場的束縛,并為市場力量影響農(nóng)村創(chuàng)造了條件。而集體與農(nóng)戶“統(tǒng)分結合”設計中“統(tǒng)”的一端,即村集體發(fā)揮組織農(nóng)戶的基礎與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切實的資源保障和制度保障(仝志輝、溫鐵軍,2009)。因此,行政村雖然被要求成為經(jīng)濟上的集體單位和政治上的自治單位,但是其變遷前景實際上卻具有某種不確定性。改革30年來,對于行政村形態(tài)的村落共同體而言,顯然有一些力量在推動村落共同體的強化,有一些因素則在發(fā)揮瓦解“集體”的作用,村落共同體不能不進入村集體與傳統(tǒng)共同體之間的不確定地帶(毛丹,2008)。
就村莊與市場關系而言,改革以來既保持村集體又發(fā)展農(nóng)村與市場的聯(lián)系,形式上有利于發(fā)展村落共同體與大社會的聯(lián)結,但是卷入村莊經(jīng)濟關系重建的三種力量——資本、農(nóng)民、政府——對于市場經(jīng)濟及村落共同體的態(tài)度、要求顯然不一樣。如前文所論,資本在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農(nóng)村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斷然不會顧忌農(nóng)業(yè)的弱質(zhì)和農(nóng)民的弱勢,按其習性只是要利用農(nóng)業(yè)的弱質(zhì)和農(nóng)民的弱勢,把農(nóng)民從村落共同體中分解為單個、廉價的勞動力,去獲取資本最大收益。而農(nóng)民對于市場經(jīng)濟的態(tài)度是隨條件而變化的,即對于市場懷抱著一種安全經(jīng)濟學邏輯,活不下去的時候會做出各種方式的反叛,僅有糊口條件時采取生產(chǎn)消費均衡模式,在條件具備時則接受和進入市場經(jīng)濟。政府則抱有經(jīng)濟繁榮與政治穩(wěn)定的雙重標準,在對待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農(nóng)村與市場的關系上,客觀上面臨五種選擇可能:壓榨剝削“三農(nóng)”,任其暴露在市場,對三農(nóng)實行半保護,保護三農(nóng),用各種方式提升農(nóng)民進市場的能力。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的政府政策選擇顯得更加困難些,通常很難簡單采取一種選擇,推動村莊經(jīng)濟轉型的各項改革政策不能不在非市場化、市場化與保護農(nóng)民進市場之間不斷尋求平衡點。于是,在重建村莊與市場的關系過程中就產(chǎn)生了一些相互沖突、相互牽扯的力量,一方面形成了分解村落共同體,把村莊打散進入市場的力量、形式與過程,例如,鄉(xiāng)村工業(yè)化并最終實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商品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進城打工與遷離、撤村建居等等,以及與此伴生的農(nóng)村勞動力從農(nóng)戶單位逐漸轉向以勞動力個體為單位。另一方面,它也促成村莊、農(nóng)戶面對市場采取各種自我保護辦法,例如,土地制度改革因突出考慮農(nóng)地對農(nóng)民的社會保障功能而步伐較小,采取農(nóng)村新合作,村集體經(jīng)營及其轉化問題受到關注,經(jīng)濟與村社區(qū)繼續(xù)保持緊密性,進行新農(nóng)村建設等等。通常,農(nóng)業(yè)生活提供社區(qū)共同體的維系,非農(nóng)化生活及對集體政治的不信任則被引導為損壞社區(qū)共同體(Caldeira,2008)。因此,前一方面變化總體上削減村莊作為社區(qū)經(jīng)濟共同體存在的必要性,后一方面變化則使村集體、村莊共同體得到維持、強化或轉型,農(nóng)業(yè)村落共同體由此繼續(xù)扮演社區(qū)經(jīng)濟共同體單位,并替代或仍然部分替代國家實施農(nóng)村公共物品與服務的供給,村莊仍然具有某種生命力。
就村莊與國家的關系變化的維度觀察,改革30年間的變化大致上是村莊經(jīng)歷了行政化、半行政化、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共同治理三個階段。行政化主要指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政府通過公社對村莊公共事務有直接決定權和優(yōu)先決定權。這種行政關系并不總是單向的,它也使村莊、農(nóng)民具有某種要求地方政府對村莊日常生活、命運負責的權利。
半行政化則是指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出現(xiàn)的過渡性格局,主要時間在80年代初至1998年。村莊根據(jù)“村組法”(試行)應享有自治權,地方政府則常常習慣沿用行政化時期的辦法干預村莊的生產(chǎn)、生活和公共事務,村莊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習慣地接受干預。但是受政府財力、村組法規(guī)定等限制,村莊與農(nóng)民的實際自治權在擴張,另一方面村莊公共供給方面受政府支持的力度也相應下降。共同治理則是村組法正式實施以后呈現(xiàn)出的國家與村莊關系的某種新趨勢。這個時期從1998年延續(xù)至今,村莊與國家相互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趨向明確,各自的權力邊界日益明晰,在村莊自主事務的范圍也得到了國家法律和實踐的尊重;與此同時,政府也趨向于承擔村莊的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服務、社會安全網(wǎng)構建等方面的部分責任,把農(nóng)民、農(nóng)村重新納入國家建設的議事日程。三個階段的總體趨勢,形式上有利于行政村成為自治的農(nóng)村社區(qū)政治共同體。但是,由于在地方政府與村莊的關系調(diào)整過程中,農(nóng)民農(nóng)村始終處于關系弱端,村落作為自治的社區(qū)共同體的前景仍具有不確定性;由于自治的社區(qū)政治共同體究竟基于社群主義還是個人主義的選擇不明晰,它究竟能否成長為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和重要部分,也存在著不確定性;甚至,由于行政村的撤并歸的權力掌控在政府手中,村落作為自治的社區(qū)政治共同體有沒有將來,還有待于國家對于村莊存在的必要性做出清晰的總體定位。
就村莊與城市的關系觀察,行政村作為社區(qū)共同體有沒有確定的前景,一方面取決于國家在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同時,是否同時發(fā)展鄉(xiāng)村社區(qū),另一方面取決于國家能否在解決城鄉(xiāng)社區(qū)的經(jīng)濟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發(fā)展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既非消滅村莊,也非城鄉(xiāng)隔離,而是建立一種有機聯(lián)系城鄉(xiāng)經(jīng)濟和城鄉(xiāng)社區(qū)的銜接帶。它在理論上是指:(1)在相對消極的意義上,承認城鄉(xiāng)經(jīng)濟、城鄉(xiāng)社區(qū)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是普遍現(xiàn)象,而不是發(fā)展中國家所獨有。(2)在積極的意義上,承認經(jīng)過對農(nóng)村社區(qū)基礎設施的大幅度改善,確立城市和村莊之間的路、訊、人、貨四暢通,可以達到城鄉(xiāng)社區(qū)生活條件的基本均等;依然存在的村莊,主要是為依然存在的農(nóng)業(yè)從業(yè)人員提供便利的社區(qū)條件,并且向城市中選擇鄉(xiāng)村生活的返郊、返村的人口開放;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zhèn)、中心村和其他村莊等,形成一個經(jīng)濟上互為支持和補充、文化風格不同但是彼此平等、社區(qū)基本生活類型不同但品質(zhì)差別并不懸殊的鏈接帶,各自都是這個銜接帶上不可替代的紐結點(毛丹,2009)。改革中前期,國家整體上偏向于勞動力轉移路徑。2000年以后,在統(tǒng)籌城市、改善農(nóng)村社區(qū)生產(chǎn)生活條件方面的一系列政府舉措,有利于觸發(fā)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帶的議程。一個充滿活力的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帶意味著村落共同體的重生,村落共同體的轉型最終能否完成,需要以此為檢驗尺度。
但是,國家目前對于這個路徑的涵義、進程和前景并不清晰。換句話說,如果把農(nóng)村社會30年的變遷放在村莊與市場、與國家、與城市社會三重關系轉變中考察,幾乎可以說村莊正在經(jīng)歷從農(nóng)業(yè)共同體到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帶之弱質(zhì)自治社區(qū)的大轉型,即:(1)經(jīng)濟共同體轉型——基于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半市場化、半受非市場化保護的政策環(huán)境,以及雙層經(jīng)營而農(nóng)戶經(jīng)營實際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村莊從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大隊,轉向具有不確定性的社區(qū)經(jīng)濟共同體。(2)治理共同體轉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實踐,村莊有可能從國家的基層治理單位轉向國家與社會共同治理的單位。(3)村莊作為農(nóng)民社區(qū)的轉型——從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區(qū)有可能轉向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帶的弱質(zhì)端。以上轉變究竟以何種形態(tài)實現(xiàn),既取決于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對國家、市場、城市的態(tài)度,更取決于國家、市場、城市對農(nóng)村的態(tài)度。從政策社會學的角度說,政府如果期望村落共同體在組織農(nóng)村人口、增長經(jīng)濟方面長久而穩(wěn)定地發(fā)揮作用,固然要幫助村莊擔負起社區(qū)經(jīng)濟共同體、社區(qū)治理共同體的職責,更要幫助村莊朝著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的方向建設,使村莊成長有一個明確的未來(毛丹,2008)
中國的村落共同體正站在十字路口。依賴慣性繼續(xù)向前滑可能行之不遠;向左轉,前景是確立城鄉(xiāng)銜接,形成村落共同體與城市的聯(lián)合體;向右轉,則是聽任市場力量分解村落共同體,一股腦驅使農(nóng)民變成城市的勞動力商品。而政府在政策選擇方面又何嘗不是站在十字路口?在此意義上說,政策社會學有必要清楚地呈現(xiàn)以下兩個基本判斷。
第一,城鄉(xiāng)和區(qū)域發(fā)展都將極其依賴于城鄉(xiāng)之間的銜接,保障村落共同體與大社會、與城市社區(qū)形成聯(lián)合體。1994年以來,這一政策主張已經(jīng)受到聯(lián)合國人類居住項目的持續(xù)倡議。2000年7月有1000個城市代表參加的城市未來全球大會,曾發(fā)表“關于城市未來的柏林宣言”(Virchow 2001:367-368),強調(diào)重新認識城市與區(qū)域、城鄉(xiāng)之間以及偏遠地區(qū)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倡言從城鄉(xiāng)分離轉向城鄉(xiāng)合作,使村莊最終具備城市的品質(zhì),城市地區(qū)也呈現(xiàn)鄉(xiāng)村的特質(zhì),促使城鄉(xiāng)分離(rural2urban divide )越來越被區(qū)塊(regional agglomeration )所取代,否則將不利于城市問題解決,不利于解決人口單向流向城市尋找工作機會而產(chǎn)生的問題,并且會使鄉(xiāng)村地區(qū)在全球化過程中更加被邊緣化——生活在這些村莊里的是被全球化經(jīng)濟排斥在外的老人、孩子以及那些缺乏城市工業(yè)與服務部門的職業(yè)技術者(Sheng Mohit,2001)。從這些研究中應該認識到:中國的城鄉(xiāng)銜接與區(qū)域發(fā)展的基礎,是給農(nóng)村社區(qū)提供充分有效的基礎設施、服務,以及道路、運輸、通訊條件和其他公共物品,這是使村莊與城市消除傳統(tǒng)區(qū)分的根本基礎。在此意義上說,中國農(nóng)村改革以來推動鄉(xiāng)村的小型企業(yè)、發(fā)展鄉(xiāng)村地區(qū)的非農(nóng)職業(yè)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僅此并不夠;著力發(fā)展農(nóng)業(yè)和商品農(nóng)業(yè)也是重要的,但是僅此也不夠。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專家萬馬麗所具體描繪的“鄉(xiāng)村基礎構造、經(jīng)濟活動與城鄉(xiāng)連接的框架”,有助于表明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發(fā)展村莊共同體與社會的聯(lián)合體所需的要素(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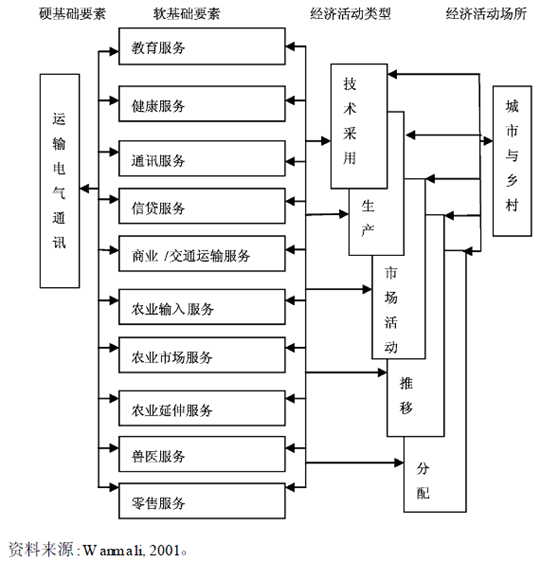
第二,依“過海比喻”,推進城鄉(xiāng)社區(qū)銜接如造跨海大橋。這個工程的主體首先是政府,即城鄉(xiāng)銜接需要政府積極干預,上述鄉(xiāng)村基礎建設雖然可以由政府和非政府提供,但是政府需要首先承擔責任。積極的政府干預是必需的,因為減少干預或不干預就是一種干預。如研究者所批評的,1980年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在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方面紛紛放棄凱斯主義經(jīng)濟學積極干預的立場和政策,退出對農(nóng)村經(jīng)濟事務的調(diào)節(jié)、計劃、供給輸入,放棄為農(nóng)村地區(qū)貧困人口積極提供福利。但是,這種新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家所呼吁、贊賞的轉變,實際上意味著國家轉而代表資本進行干預(例如以立法方式重新變更土地制度)。而資本在農(nóng)村的積極干預,則到處引起農(nóng)民的四種形式的反抗,包括反對原始積累、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非資本主義鎮(zhèn)壓和資本所引起的生態(tài)條件、反對民主國家對資本的運用,等等,結果又導致新自由主義國家要求一個干預性的國家去應對這些問題(Das ,2007)。就中國的農(nóng)村社區(qū)共同體的發(fā)展而言,如果國家不能明確地告別新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的立場,沿著推進城鄉(xiāng)銜接的路徑和方向,轉而用加強農(nóng)村基礎建設、以服務為中心介入農(nóng)村社區(qū)發(fā)展,那么就很難避免加快城市化與建設新農(nóng)村兩大國家戰(zhàn)略之間出現(xiàn)斷裂,新農(nóng)村建設也很難避免迷失方向與前景。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學中國社區(qū)建設研究中心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wǎng)轉自:《社會學研究》2010年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nèi)容!)



